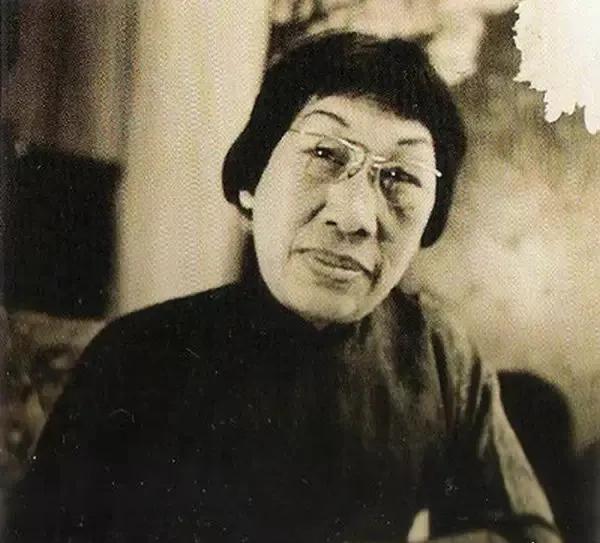手往她裆下一摸,完了。 藏不住了。 那鬼子兵脸上那股子兴奋劲儿,比南京冬天的风还扎人。他一把就把她往墙根底下拖。 那年她才19岁,金陵女大的学生。头发剪得跟狗啃似的,脸上抹满了锅灰,就为了装个男的,活命。 身上这件粗布褂子,是哥哥拿命换的。 他替她挡了子弹,倒下前,死死盯着她,就两个字:“活路。” 现在,这件褂子,也快保不住了。 冰冷的墙砖硌着后背,她脑子里嗡的一声,全是哥哥倒下的样子。 人到了绝境,哪来的力气? 可就是没力气,也得挣。她猛地一口,死死咬住那只伸过来的脏手。 满嘴都是铁锈味儿。 真他妈的疼,也真他媽的爽。 一记耳光扇过来,天旋地转。 但就在她以为自己要死在这儿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喊,外国口音。 一个穿着长裙的外国女人,疯了一样跑过来,手里还挥着个啥。 后来才知道,是她们学校的外籍老师,在“安全区”附近捞人,捞一个是一个。 那鬼子,居然有点怕。骂骂咧咧地松了手。 她被那个外国女人搂着,带回了所谓的“安全区”。 挤满了人,每一张脸都写着两个字:麻木。 一碗滚烫的稀粥递到手上,眼泪“吧嗒”一下就掉进去了。 她想起了爹的书房,想起了哥哥塞给她的糖。 家没了,亲人也没了。 她活下来了。 把哥哥那件破褂子叠得整整齐齐,贴身藏着。 她说,这不是一件衣服,这是我欠我哥的一条命。我得替他,替我爹,替所有倒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好好活着。 后来,她也成了一名老师。 她总跟学生讲,别信什么岁月静好。咱们脚底下这片地,曾经被血泡透过。 有些事,你要是忘了,那跟亲手把祖宗的坟刨了,没啥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