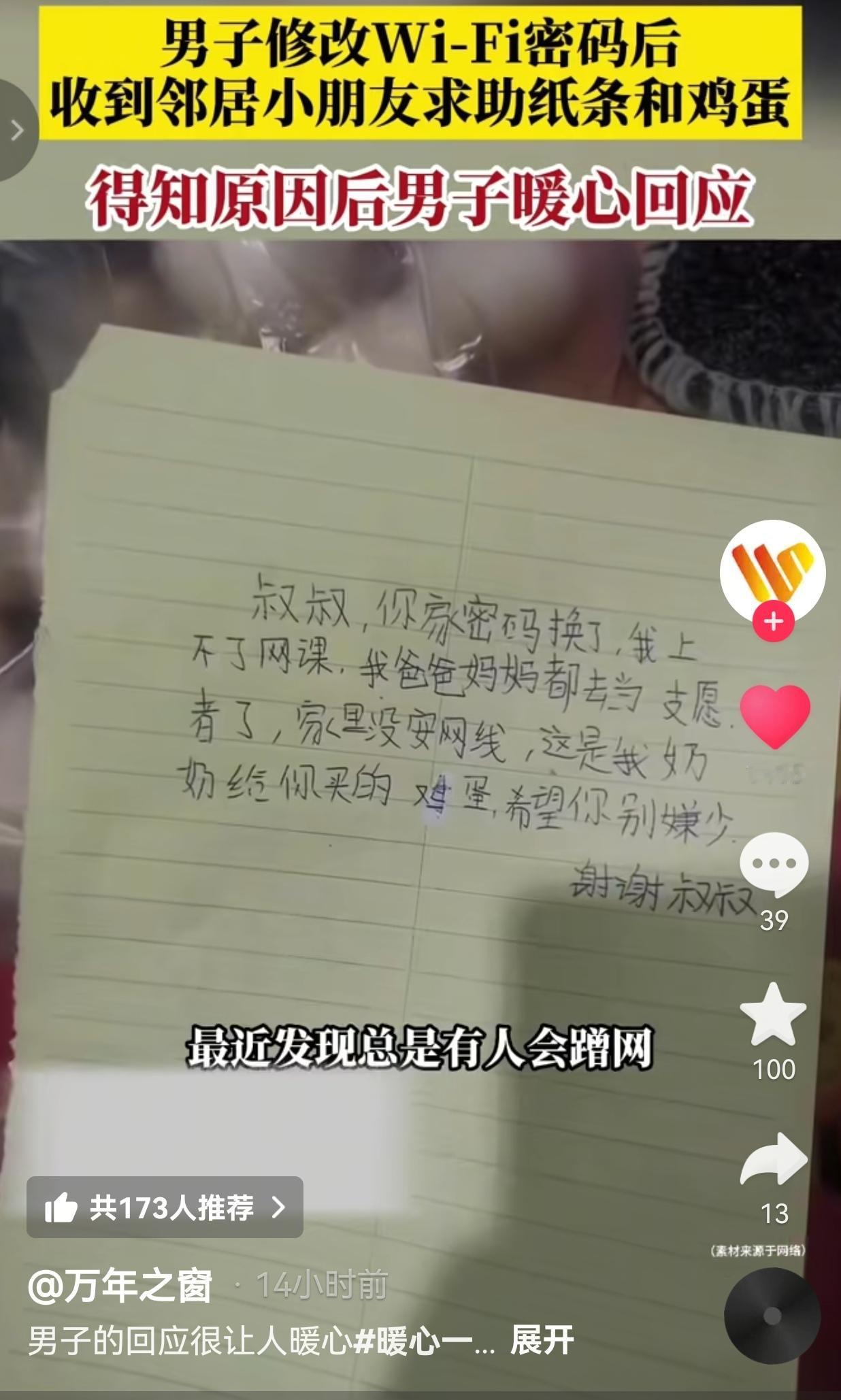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1952年的北京秋日,阳光把琉璃厂的青石板晒得暖融融的。史树青揣着个布包,慢悠悠地在胡同里晃——包里是刚收来的两枚明代铜钱,沾着点泥土,却透着温润的包浆。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他最大的乐事就是在这些烟火气里“淘宝”,裤脚总沾着灰,布鞋磨得发亮,眼神却比谁都亮。 转过一个拐角,胡同口蹲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子,面前摆着块旧木板,上面摊着几幅卷着的字画,风一吹,纸角簌簌地响。“先生看看?家里老人留下的,换点钱给孩子看病。”女子声音发涩,手里还攥着块干硬的窝头。 史树青本想走,目光却被最底下那幅画勾住了。画轴缠着旧麻绳,看着不起眼,露出的一角却透着暗沉的朱砂色。他蹲下身,指尖捏着画轴边缘轻轻一挑,“哗啦”一声,画在木板上铺开——绢本泛黄,却能看出细密的织纹,上面画着个穿皮袍的男子,眉眼锐利如鹰,腰间悬着弯刀,背景是起伏的草原,笔触沉郁,带着股苍茫气。 “这画……”史树青的手指突然顿住,呼吸都屏住了。他研究元史多年,见过无数仿品,可这画里的细节太特别:男子的皮袍边缘绣着狼头纹样,腰间的蹀躞带上挂着枚金符,正是元代皇室特有的“虎头金牌”。更奇的是笔触,看似粗犷,衣褶处却藏着极细腻的晕染,带着典型的“院体”风格,绝不是民间画匠能仿的。 “多少钱?”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常,指尖却在微微发颤。 女子抬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画,小声说:“您给……给三块钱就行,够买两副退烧药的。” 史树青赶紧从兜里摸出三张纸币,塞到女子手里,小心翼翼地把画卷好,揣进布包最里层,像是捧着块烫手的烙铁。转身往回走时,他脚步都有些飘,满脑子都是画中男子的眉眼——那神态,那气度,太像史料里记载的成吉思汗了。可成吉思汗不是立下“四不”遗嘱,不许画像吗? 回到家,史树青关起门,把画铺在书桌上,就着台灯一点点细看。他用放大镜瞅绢本的纤维,对着阳光看墨色的层次,甚至翻出《元史》里的服饰记载比对。越看心越跳:这画的绢本是元代特有的“库绢”,墨里掺了麝香和朱砂,是宫廷画师常用的技法,尤其是男子耳后的那道小疤,竟与波斯史料里提到的“成吉思汗少年时被异母弟所伤”的记载对上了。 “难道是……”他猛地拍了下桌子,差点碰倒墨水瓶。或许是元代中后期,朝廷为了彰显先祖功绩,悄悄命画师根据传闻绘制的?毕竟成吉思汗的“四不”遗嘱,到了后世难免松动。 1962年,史树青把这幅画捐给了国家博物馆。专家组鉴定时,连见惯了珍宝的老馆长都激动得手抖:“没错!是元代的!你看这笔触,这绢本,假不了!” 开馆那天,这幅成吉思汗画像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玻璃展柜里,泛黄的绢本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画中草原的风仿佛还在吹。史树青站在展柜前,想起十年前那个胡同口的秋日,想起那三块钱换来的震撼,突然觉得,那些埋在民间的宝贝,就像散落在尘埃里的星星,总得有人弯下腰,才能让它们重新发光。 而这幅打破“四不”遗嘱的画像,就这么静静立在那里,诉说着八百年前的传奇,也记下了一个教授在胡同里的偶然发现——历史的巧合,有时就藏在这不经意的一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