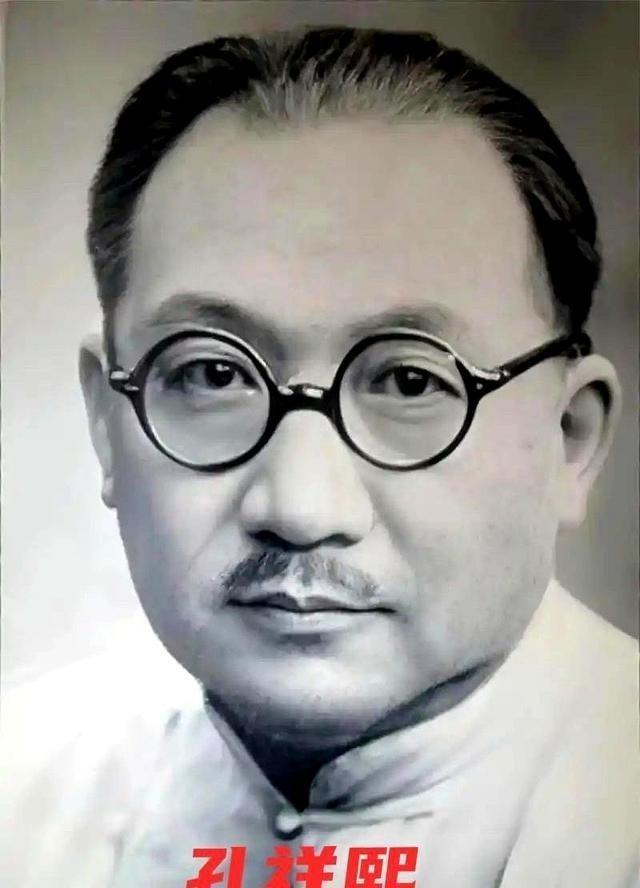1981年,作家黄宗英说:“都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 1978年,那时候的遇罗锦,浑身带着那个时代的伤痕,哥哥遇罗克因为那篇著名的《出身论》,批判“血统论”而丢了性命;她自己也因为几句日记被定性为“思想反动”,在这个特殊的年月里劳教了三年。 回到北京时,她是一个无户口、无工作、无住处的“三无人员”。 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工人蔡钟培,老蔡条件不算差,手里有间房——这意味着能落户口,在那个连生存缝隙都极其狭窄的年代,婚姻成了一场赤裸裸的“互助协议”,蔡钟培图个有文化的媳妇,哪怕是再婚;遇罗锦图一张能留在北京的床铺。 必须承认,这桩后来被骂作“忘恩负义”的婚姻里,蔡钟培确实付出了真心和汗水,婚后两年,他跑断了腿帮遇罗锦落实户口、找工作,甚至连遇罗克平反的一摞摞手续,都是他出力跑下来的。 可遇罗锦偏偏是个“异类”,肚子吃饱了,她那颗属于作家的心又活了,她不想把婚姻仅仅当成生存的防空洞,1980年5月16日,一纸诉状递进朝阳区法院,理由震碎了当时人们的认知:没有共同语言。 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乃至看到报纸的全国读者,愤怒几乎是一边倒的,蔡钟培觉得委屈:我为你掏心掏肺,现在你日子安稳了,哥哥平反了,就想把我踹了?这不就是当代的“女陈世美”吗? 当时恰逢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感情确已破裂”刚成为法定离婚标准,负责一审的助理审判员党春源是个大胆的人,他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恩格斯的话,试图从理论高度证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判,支持了遇罗锦,却也捅了马蜂窝。 蔡钟培不服上诉,案件被北京中院发回重审,《新观察》和《民主与法制》杂志开辟专栏,把这事摊在桌面上让全民讨论,编辑部的信箱被各地读者的来信塞爆了,有人甚至专程把信寄到法院,甚至有不少也想离婚的男男女女拿着报道去当地法院排队。 真正把遇罗锦推向深渊的,是她的诚实,她不像传统受害者那样忍气吞声,而是拿起笔,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 在书里,她毫无保留地解剖了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结婚的痛苦、对这桩交易性质婚姻的厌恶,甚至坦诚了精神上的出轨和对婚外情感的渴望。 这份赤裸裸的坦白,对于刚刚打开国门、思想还裹着小脚的社会来说,太超前也太刺眼了,读者惊呆了,没想到有人敢把“虽然我有罪,但我不想为此凑合一辈子”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代价随即而来,尽管当时也有清醒的声音——作家黄宗英在一次作协的颁奖座谈会上,看着没能获奖的遇罗锦,联想起三十年代上海滩同样因为婚恋问题被非议的上官云珠。 她悲愤地把钢笔递给遇罗锦,当众质问:“怎么都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反倒容不下一个遇罗锦?”黄宗英不明白,为什么物质生活进步了,人们对他人的宽容度反而比旧时代还窄? 但微弱的支持挡不住汹涌的巨浪,法院虽然最终在调解下判决离婚,却也没忘在结案总结里给舆论一个交代,暗示是因为遇罗锦“社会地位变了”才导致婚变。 随之而来的是更严厉的封杀。她在《花城》杂志发表的续作《春天的童话》,直接导致该杂志主编、副主编被调离,整个编辑部写了三个月的检查,刊物被迫刊登自我批评并禁销,她在北影厂筹备的电影剧本也没了下文。 原本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一夜之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问题人物”。 1986年,她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未解的委屈,申请政治庇护,远走德国,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她后来又结了两次婚,最后和一个德国人过上了那种她一直渴望的、单纯的、没有那么多算计的日子。 信源:遇罗锦离婚嫌对方文化低 在道义上被判“死刑”——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