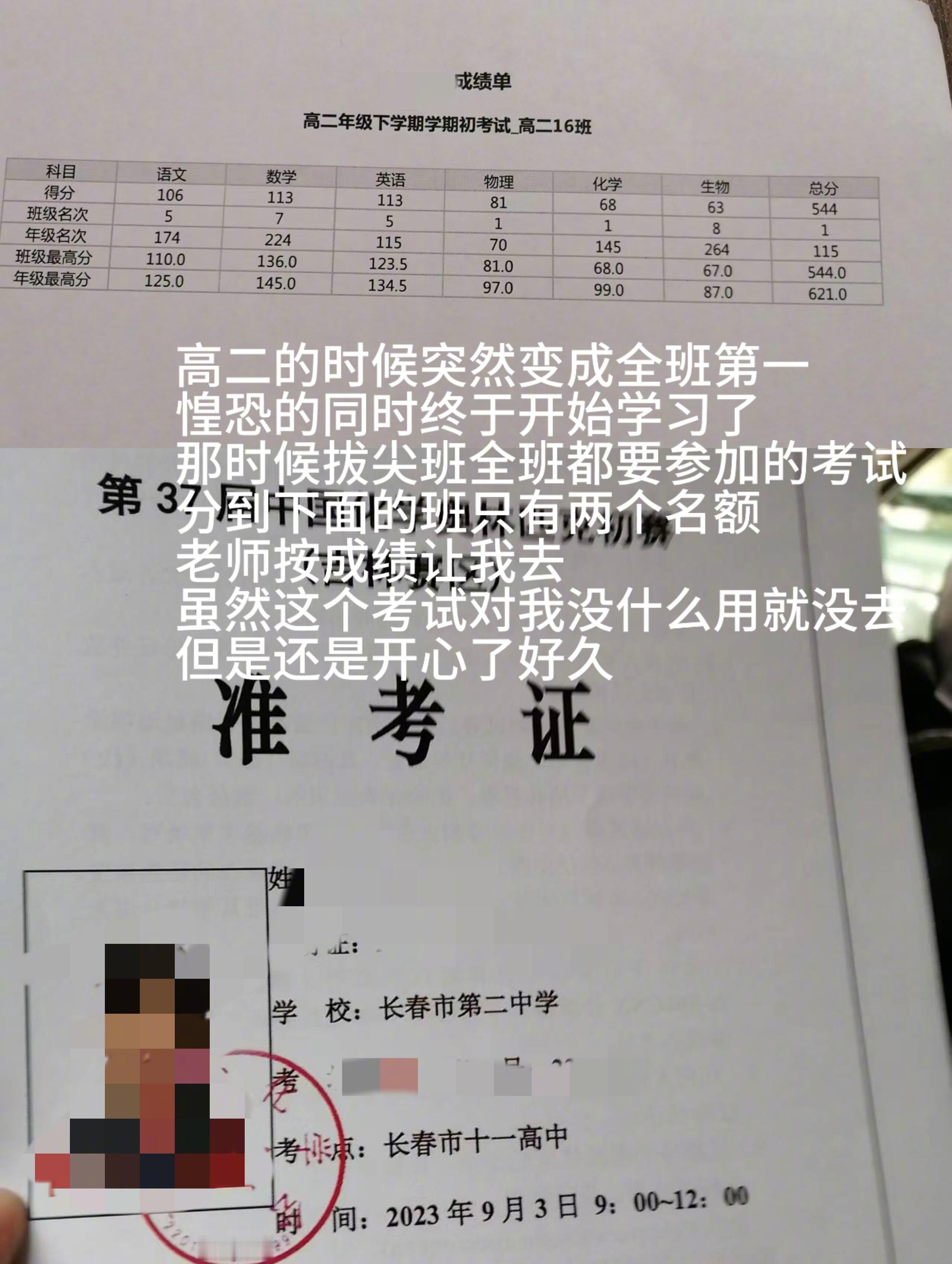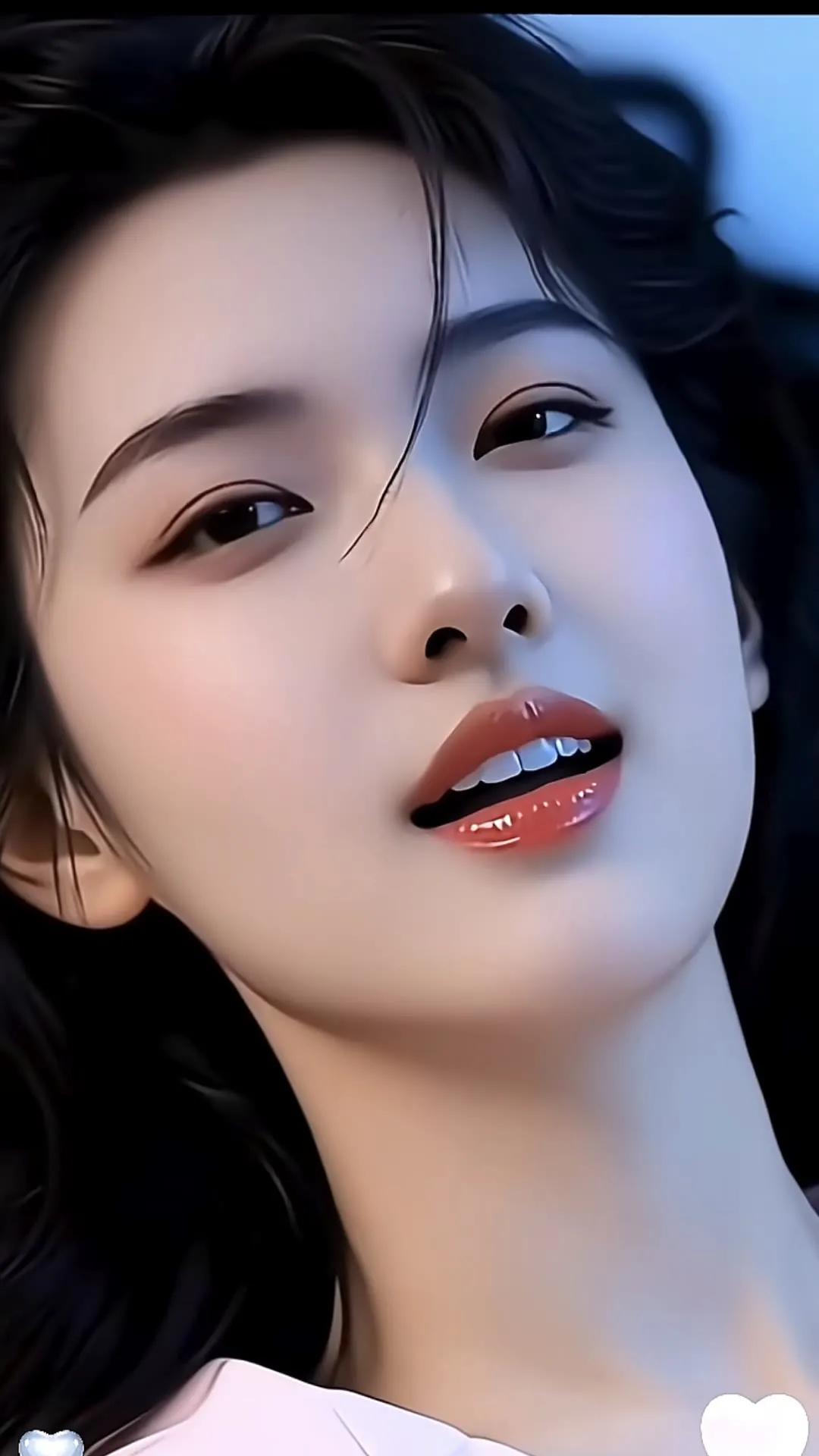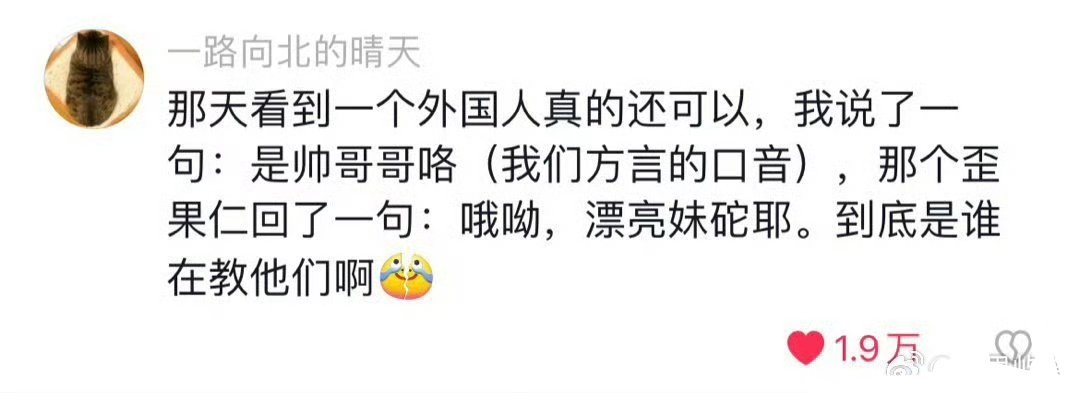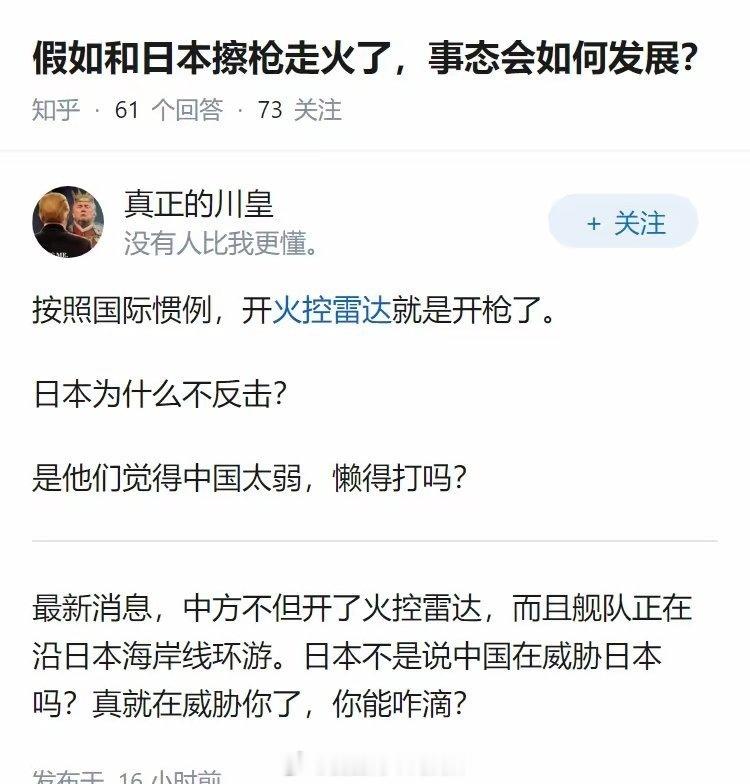快90岁的齐白石,使出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将25岁的女徒弟新凤霞,拉进一间黑屋子。 门“哐当”一声合上,外头的说笑声、戏曲调门儿瞬间隔远了。屋里暗,只有木格窗棂透进几道蒙蒙的光,能看见灰尘在那光里慢悠悠打转。新凤霞心里突突跳,倒不是怕,是摸不着头脑。老师的手还攥着她手腕呢,那手干瘦,却像老树根似的,箍得紧。 “丫头,别吱声。”齐白石的声音哑哑的,凑近了,带着点墨和旧纸张的味道。他另一只手在怀里摸索半天,掏出来的不是画稿,是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头是几块咬过的、看着挺硬的点心。“藏着给你留的,”他压低嗓子,“他们外边闹,吵得我脑仁疼。你也饿了吧?唱了一上午了。” 新凤霞愣住,看着那几块或许是他自己舍不得吃、攒下来的点心,鼻头忽然有点酸。这黑屋子,原来是个“偷嘴”的避难所。外界对齐白石的传言可多了,说这老头儿脾气怪,抠门,对年轻漂亮的女徒弟指不定有啥心思。可眼前呢?就是个怕热闹、想偷偷给徒弟塞点零嘴儿的孤僻老头。 齐白石自己蹭到一张旧藤椅上坐下,示意她也坐。屋子堆满杂物,画具、宣纸、还有不少看来是舍不得扔的瓶瓶罐罐。“他们啊,”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就知道看画。虾怎么动,虫怎么跳,荷花底下有没有泥……问个没完。”他斜眼瞅瞅新凤霞,“你唱戏的,懂不懂?那‘劲儿’不在锣鼓点儿最响的时候,常在嗓子里含着、还没全放出来那一下;笔也一样,最活的鱼,往往就画它要摆尾还没摆的那一瞬。” 这话钻进新凤霞耳朵里,像给她心里亮了盏小灯。她自个儿琢磨戏,不也总追求那个“未完成”的韵味么?唱得太满,反而没意思了。这黑屋子,一下子从偷吃零嘴的角落,变成了传艺的密室。没有旁人瞻仰大师的风采,只有一个老画匠对着一个小艺人,讲最朴素的道理。 那时候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一个年近九旬的老头,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关在黑屋里,哪怕只是说说话、讲讲画,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齐白石不知道吗?他精着呢。可他似乎不在乎,或者,他太在乎另外一些东西了。他看新凤霞,或许不止是看一个女徒弟,更是看一块难得的“材料”,一副能懂他笔墨里那份“活气”的灵性嗓子。艺术到了顶尖处,门类反而通了,画戏不分家,要的都是那股子生命力和刹那的神韵。 他絮絮叨叨,讲他小时候放牛,看水塘里小虫怎么打架;讲他做木匠,刀刻进木头里的手感。新凤霞渐渐忘了开始的紧张,也跟着说,说她们练功的苦,说台下看客的眼神,说一句唱词怎么改才能更“入味”。这一老一少,在昏暗的光线里,聊得忘了时辰。那些关于年龄、性别的窥测与猜疑,被这满屋的陈旧气息和偶尔飞扬的、带着灵感的尘灰,隔在了门外。 要说齐白石没点偏脾气,那不可能。年纪大了,越发像个孩子,喜欢就是喜欢,厌恶也摆脸上。他对这个关门女弟子,是实打实地爱护,这种爱护混合着对艺术传承的焦灼,显得有点笨拙,甚至不顾场合。拉进黑屋子这举动,在外人看来惊世骇俗,在他自己,可能就像随手扯了张宣纸,要即兴涂抹几笔一样自然——心里有话,得赶紧说给懂的人听,哪管它是在明处还是暗处。 艺术传承这事儿,有时候真不是在敞亮的大厅里鞠躬奉茶完成的。它可能在某个午后杂乱的后台,可能在一封字迹潦草的信笺里,也可能,就在这么一间堆满杂物的黑屋子中,伴随着几块硬点心和压低嗓音的交谈。那些最精髓的、近乎本能的感觉,往往需要避开喧嚣,在一种近乎“私密”的氛围里,才能悄然渡让。 门终于开了,光线涌进来。外头的人或许还在揣测里头发生了什么。只有新凤霞知道,手里攥着的不是点心屑,是比金子还重的几句话。齐白石背着手,溜溜达达又混进人群里,好像刚才啥也没干。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