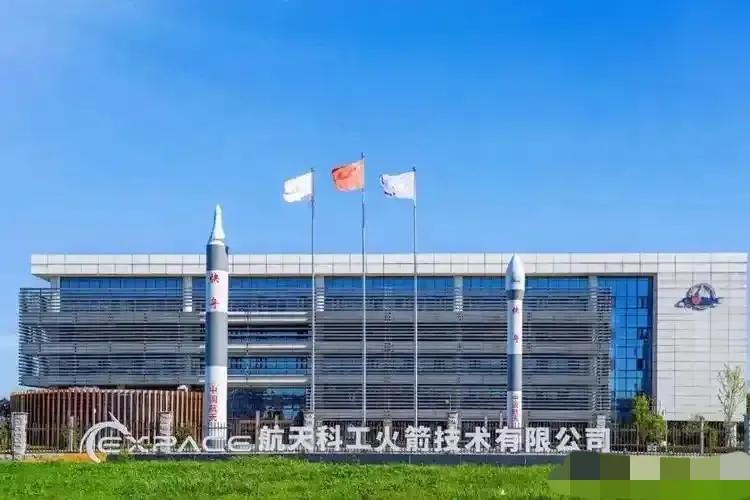1988年,武汉女教师在医院生下一个小男孩。谁知,丈夫突然在她耳边说:“老婆,把氧气管拔掉吧,我们还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女教师脸色大变,怒斥道:“我真后悔嫁给你!” 那时邹翃燕29岁,在幼儿园教孩子们唱儿歌,工资刚够买奶粉。怀孕后她没请过一天假,每天早上骑车穿过积着雨水的柏油路,车筐里装着给孩子们折的纸青蛙。产检本上“一切正常”的字样还没干,产房里医生的一句话却让世界塌了——“宫内窒息太久,重度脑损伤,抢救意义不大”。 丈夫收拾行李时,她抱着襁褓里插着氧气管的婴儿坐在床边。洗衣机、电风扇、录音机被陆续搬出门,最后他放下38块零钱和两床起球的旧棉被,“你想救就救,别指望我”。她没回头,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回了娘家的老房子。 孩子取名丁峥,字典被她翻得掉了页,就为“铮”字——要活得响亮。一岁时他连纸片都抓不住,她从幼儿园带回废试卷,让他每天撕,从一张撕到满床碎纸,手指磨出茧子才终于能捏住积木。两岁半站着就晃,她跪在床边给他捏脊,六小时不歇,孩子背上青紫一片,哭声把邻居都惊醒,她咬着牙说“妈妈在”。 最慌的是智力测试。她举着红绿色气球在他眼前晃,丁峥的眼神跟着气球转,那一刻她蹲在地上哭了——儿子脑子没坏。后来医院每年测智商,12年的数据都写着“正常”,只是小脑神经受损,动作比同龄人慢半拍。吃饭她偏要教筷子,打手心的竹尺断了两根,“妈不想你以后在饭桌上低着头”。 上学成了攻坚战。她揣着病历跑了七所小学,校长们看一眼丁峥走路的姿势就摇头。最后一所小学的校长说“试读三天”,她在教室外站了三整天。丁峥坐在最后一排,写字比同学慢一半,她把课本重点录进磁带,让他每天坐公交时听,“别人听一遍,我们听十遍”。初三那年,他的名字出现在年级前十的榜单上,校长把奖状递给她,她蹲在操场边哭得肩膀发抖,像个丢了糖的孩子。 2007年夏天,丁峥拿着660分的高考成绩单回家,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来被她压在玻璃桌下。本科时他拿了两次国家奖学金,毕业时抱着“优秀毕业生”证书笑,她摸着证书边角,想起他撕试卷的样子。再后来,他考上北大国际法学院硕士,2016年冬天,她在菜市场买菜,广播里念着“丁峥,哈佛法学院录取”,菜篮子“哐当”砸在地上,她跪在泥水里哭了半小时,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指着墙上丁峥穿博士服的照片,“你看他笑得多亮。当年要是听了那句话,哪有现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像撒了一把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