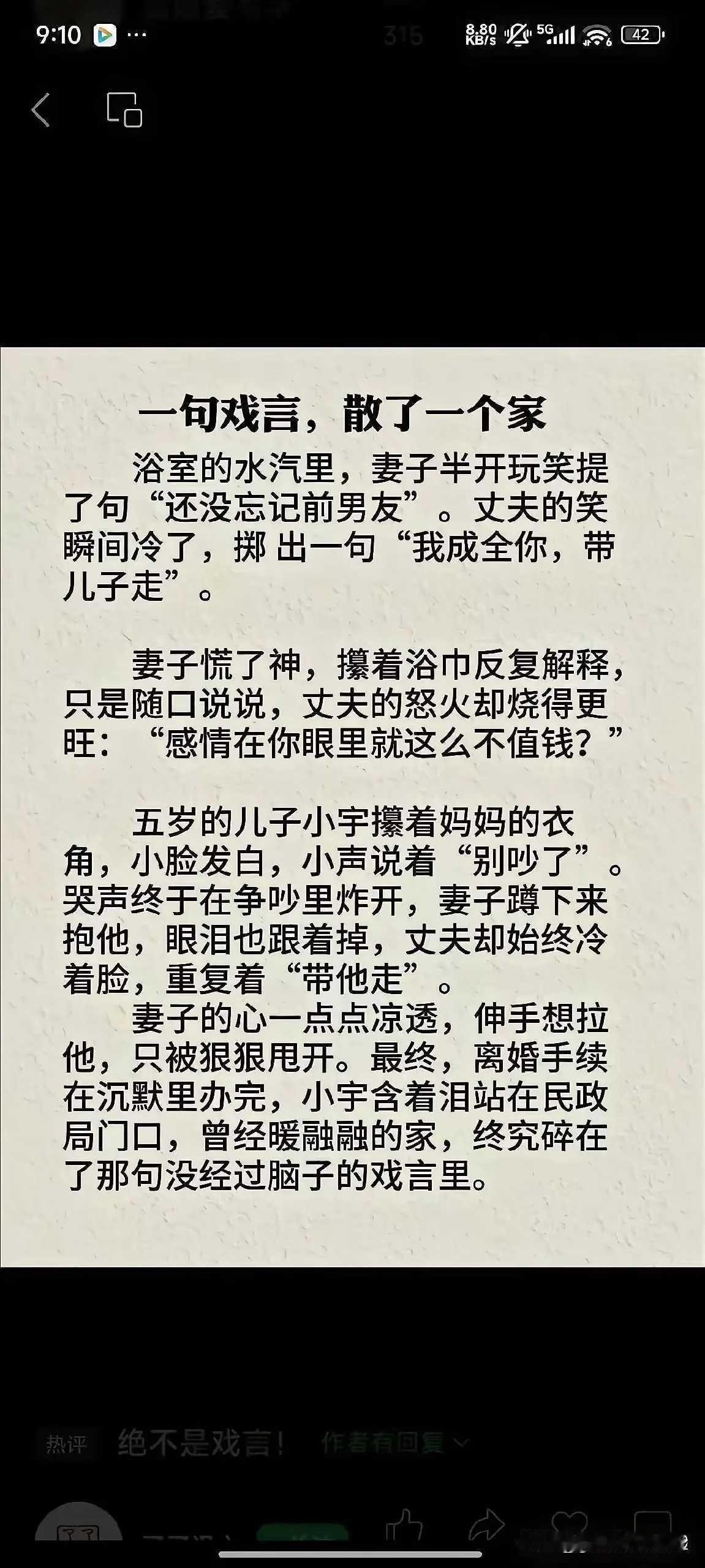1904年,通房丫李氏,站通房丫李氏,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长达33年。这日,她正在盛饭。谁知,管家突然冲进来高喊了一句,她手一歪,啪地一声碗摔落地面碎了一地。正妻刚打算开口斥责,丈夫却开怀大笑:“坐下,一同用膳! 没人知道,李氏入府那年才十二岁,是管家从城外破庙里领回来的孤女。彼时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头发枯黄打结,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顺畅,被分到正院当最低等的粗使丫鬟,每日天不亮就起身挑水、劈柴、打扫院子,夜里还要守在正妻床边听候差遣。三年后,因她手脚麻利、性子温顺,又识得几个字——那是府里老夫子偶尔教的,才被抬为通房丫鬟,从此便多了一份侍奉男主人的本分,也多了无数看不见的规矩与委屈。三十三年来,她每日天不亮就梳洗妥当,站在正厅角落等候,三餐时端茶盛饭、布菜添酒,始终脊背挺直,不敢有半分懈怠,哪怕膝盖常年酸痛,哪怕指尖被碗筷磨出厚厚的茧子,哪怕逢年过节也只能看着旁人阖家团圆,自己却连一件新衣裳都不敢奢求。她早把“低人一等”刻进了骨子里,摔碎饭碗的那一刻,她脑子里第一反应不是疼,也不是慌,而是想着这下免不了一顿打骂,或许还要被杖责后赶出府去,毕竟在这深宅大院里,通房丫鬟的性命,比一只蝼蚁强不了多少。 管家那声高喊还在厅堂里回荡:“大人!朝廷新政颁下来了!奴仆可申请脱籍,您先前吩咐打听的事儿,户部那边有准信了!” 丈夫这才收住笑声,目光落在李氏身上,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疏离,多了几分复杂的暖意。他是地方上的小官员,虽官阶不高,却也受新政风气影响,早便觉得府中奴仆制度苛责,尤其是对李氏,三十三年如一日的忠心侍奉,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先前他就暗中托人打听奴仆脱籍的章程,只是一直没有消息,今日管家带来的喜讯,恰好给了他一个抬举李氏的机会。 正妻脸上的怒意僵在原地,指尖攥着帕子微微用力。她出身世家,自幼便受“尊卑有序”的教诲,在她眼里,李氏不过是个伺候人的丫鬟,哪怕当了通房,也不配与主人同席用餐。可她也清楚,如今新政推行,各地都在放宽奴仆人身依附的限制,若是还像从前那般苛待奴仆,传出去恐落人口实,甚至影响丈夫的仕途。再者,她与李氏相处三十三年,虽平日里严苛,却也知道李氏的本分,从未有过半分逾矩之举,此刻见丈夫态度坚决,也只能压下心头的不满,冷冷地瞥了李氏一眼,没再开口斥责。 李氏僵在原地,浑身紧绷,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真的坐下,双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颤抖,碎瓷片溅到裤脚的冰凉触感,此刻竟比不上心头的慌乱与茫然。她想起二十年前,自己曾生过一个男婴,只因身份低微,孩子刚满月就染了风寒,正妻不肯请大夫,丈夫虽有怜悯,却也碍于规矩没能破例,最后孩子没能保住。那一夜,她抱着冰冷的孩子,在柴房里哭到天亮,却连一句抱怨都不敢有,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肚子里,依旧日复一日地尽心侍奉。这些年,她见过府里其他丫鬟被打骂、被发卖,也见过有人不甘屈辱偷偷逃跑,最后被抓回来打断双腿,她不敢反抗,也不敢逃跑,只能靠着“好好侍奉,或许能有个安稳晚年”的念头,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怎么?不敢坐?” 丈夫的声音温和了几分,伸手示意她坐下。李氏迟疑了许久,才缓缓地挪动脚步,小心翼翼地坐在桌子的最角落,身子依旧微微前倾,仿佛随时准备起身侍奉。她低着头,不敢看丈夫和正妻的眼睛,鼻尖却忍不住发酸,三十三年的隐忍、委屈、不甘,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了一丝慰藉。她知道,丈夫让她同席用餐,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吩咐,更是对她三十三年忠心的认可,是新政之下,小人物命运的一丝转机。 1904年的清末,正是新政推行的关键时期,废除科举、改革官制、放宽奴仆人身依附,每一项变革都在悄然改变着底层人的命运。李氏或许不懂什么是新政,也不懂什么是人身自由,她只知道,这一天,她不用再站着侍奉,不用再担心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打骂,不用再像草芥一样任人摆布。那些常年酸痛的膝盖,那些磨出厚茧的指尖,那些深夜里无声的泪水,终于在这一刻,有了被看见、被尊重的可能。 深宅大院的规矩,延续了千百年,尊卑贵贱的鸿沟,曾让无数底层奴仆看不到希望。但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一丝新政的春风,一句主人的认可,就足以照亮一个小人物卑微的一生。李氏三十三年的坚守,不是懦弱,而是底层人在苦难中挣扎的坚韧,是对安稳与尊重的朴素渴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