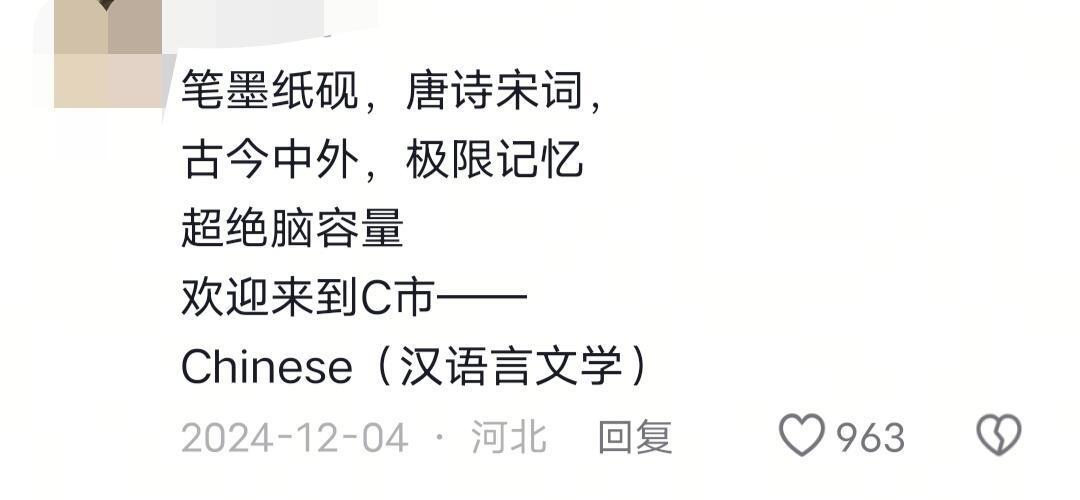1993年,6年没有收入的陈忠实在家闲坐。突然一通电话打来,接完电话后,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妻子吓得赶紧过来扶他,哪知,陈忠实却激动地说:“老婆,咱不用养鸡了!” 这是他辞职写作的第6年,家庭生计全靠妻子王翠英的工资维持,养鸡是唯一的额外收入来源。 电话铃骤响,来电为陕西作协,告知《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且获奖概率极高,奖金为5万元。挂掉电话后,他瘫坐在地,说出了让妻子热泪盈眶的话。 1965年,他发表第一篇散文《夜过流沙沟》,其后担任《陕西文艺》编辑期间,创作的《信任》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7年,44岁的他递交辞职信,核心诉求是“写一部能垫棺作枕的书”——当时他已意识到,自身短篇创作抵达瓶颈,必须寻求突破。 辞职后的生活比预想更为艰难,陈家居住在西安东郊的普通民居,三间瓦房存在漏雨问题,冬季需依赖煤炉取暖。 陈忠实将自己封闭在西厢房创作,一张旧书桌与一盏台灯构成全部创作装备。 妻子每月40多元的工资需支撑一家三口开支,还要供应儿子上大学,他只得在院内搭建鸡笼,最多时饲养30多只鸡,以鸡蛋兑换油盐,每隔一段时间售卖母鸡补贴家用。 1987年夏季,他携带笔记本进驻蓝田县档案馆,系统研读从清朝至民国的《蓝田县志》,重点抄录“贞妇烈女”“宗族纷争”等记载——这些详实的人物事迹与事件记录,成为白嘉轩、鹿三等人物的原型素材。 他还骑行自行车遍历白鹿原周边村镇,与80多岁的老者促膝长谈,搜集民国时期地租制度、宗族械斗及瘟疫流行等一手信息。 一个鲜为人知的创作细节是:《白鹿原》最初设定的主角并非白嘉轩,而是鹿三。田野调查中,他发现白鹿原的宗族族长是维系地方秩序的核心力量——无论世事动荡,族长需统筹祭祖仪式、裁决邻里纠纷、守护乡邻安全。 在蓝田县孟村,他找到一位张姓族长的后人,研读其家族传承的《族规》后,将主角调整为白嘉轩,确立“仁义白鹿原”的核心主题。 创作过程中的“自我否定”险些让他终止创作。1988年春节,他完成前10章初稿,交由陕西作协同仁审阅,有评论直言“叙事如流水账,缺乏精神内核”。 当晚,他将初稿锁入木箱,在院内蹲坐抽完两包烟。妻子并未过多劝慰,只是将热好的粥端至他面前说:“写不下去就歇歇,养鸡也能维持生计。” 次日清晨,他取出县志笔记重新梳理,决定加入朱先生这一“精神坐标”后重写。 1992年3月,48万字的初稿完成,但他认为作品仍显稚嫩,得知河南一位老中医收藏有民国时期的药方与日记后,他当即揣着家中仅有的200元钱乘火车前往。 老中医的日记详细记录了1930年关中大旱时期的社会民情,这些细节被他融入创作,如白嘉轩开仓放粮的场景、村民在灾荒中的生存状态等,显著增强了历史叙事的质感。 直至1992年10月,他才将修改后的稿件递交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的中国文坛正处于“寻根文学”的鼎盛阶段,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等作品已流行数年,但创作视角多聚焦南方地域文化。 《白鹿原》的问世,填补了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域文化书写的空白。茅盾文学奖评审组后续披露,初读便被“白嘉轩一生娶七房媳妇”的开篇震撼——以家族史承载民族史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国内文学创作中较为罕见。 1997年《白鹿原》正式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陈忠实未迁居大城市,仍居住在那座小院,仅将鸡笼拆改建成小花园。 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写道:“养鸡的六年,让我真正理解白鹿原的农民——他们的坚守与韧性,都蕴含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这种源于生活的感悟,构成作品最具感染力的内核。 《白鹿原》的走红亦推动陕西文学的崛起。此前陕西作家被称为“黄土派”,作品多聚焦农村苦难叙事。 《白鹿原》问世后,贾平凹、路遥等作家的作品获得更多关注,形成“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这一称谓由《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提出,后因陈忠实认为“征”字带有侵略性,建议改为“陕军东进”。 1995年《白鹿原》被译为日文,日本汉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百年孤独》”,二者均以家族史承载民族集体记忆。 回望1993年那通电话,背后是一位作家“破釜沉舟”的决心。当时与他同期辞职专职写作的共有3人,最终仅有他坚持到底。 被问及成功秘诀时,他答道:“并无特殊技巧,只是将他人娱乐闲聊的时间,用于研读县志、搜集民间故事。”这一表述至今仍具启示意义——所有“一鸣惊人”的成就,本质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2016年陈忠实逝世后,工作人员在其书房发现那本泛黄的《蓝田县志》,上面画满横线并附有大量批注。 那只曾经的鸡笼被陕西文学馆收藏,旁附说明牌:“这里承载过一位作家的窘迫,更封存着一部经典的创作初心。” 这或许是对1993年“不用养鸡了”这句话的最佳注解——真正的坚守,总能穿越困境抵达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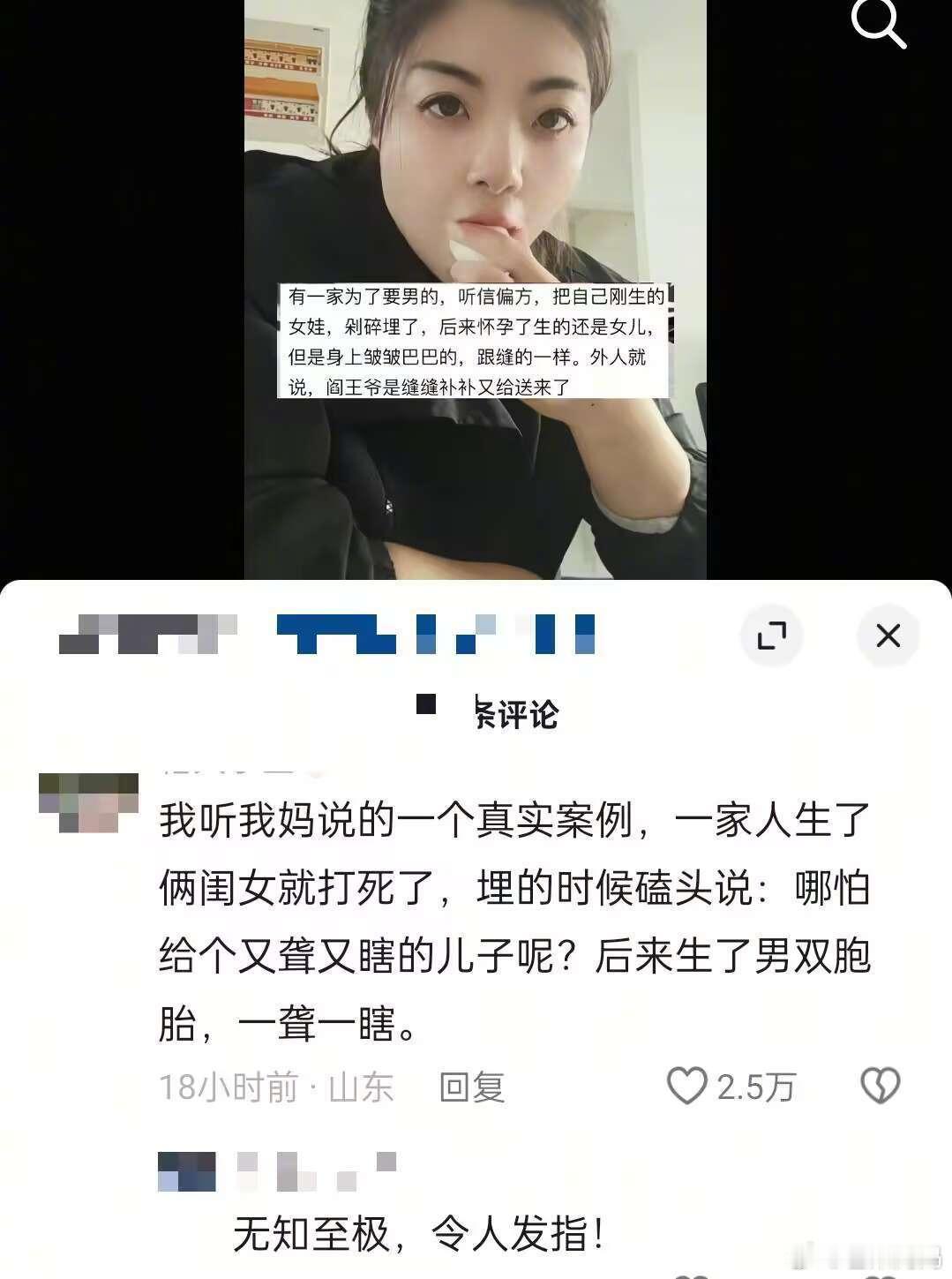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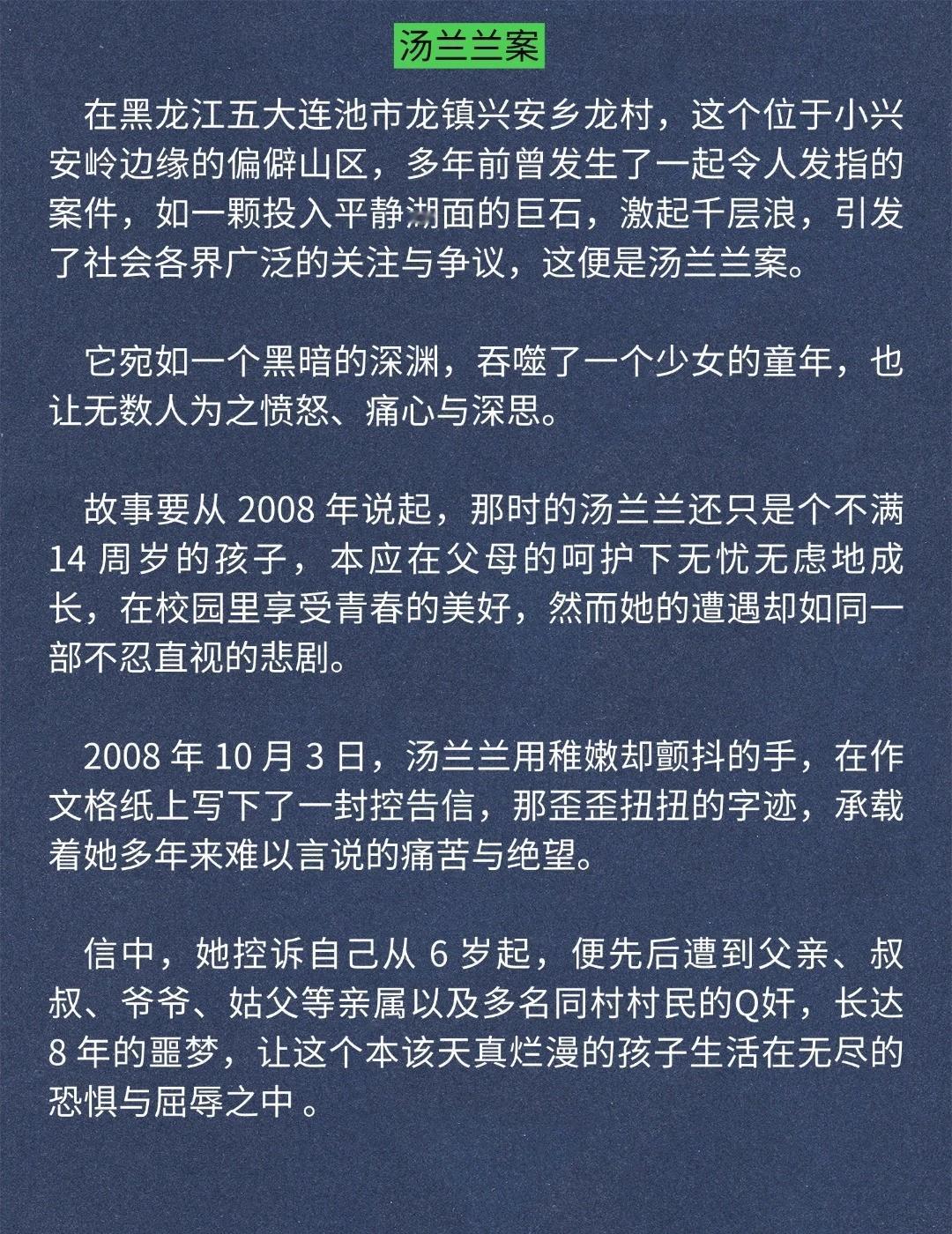
![七万骑兵?吴俊升一个师长能养的起十多万匹马?[吃瓜]](http://image.uczzd.cn/15213221908252555442.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