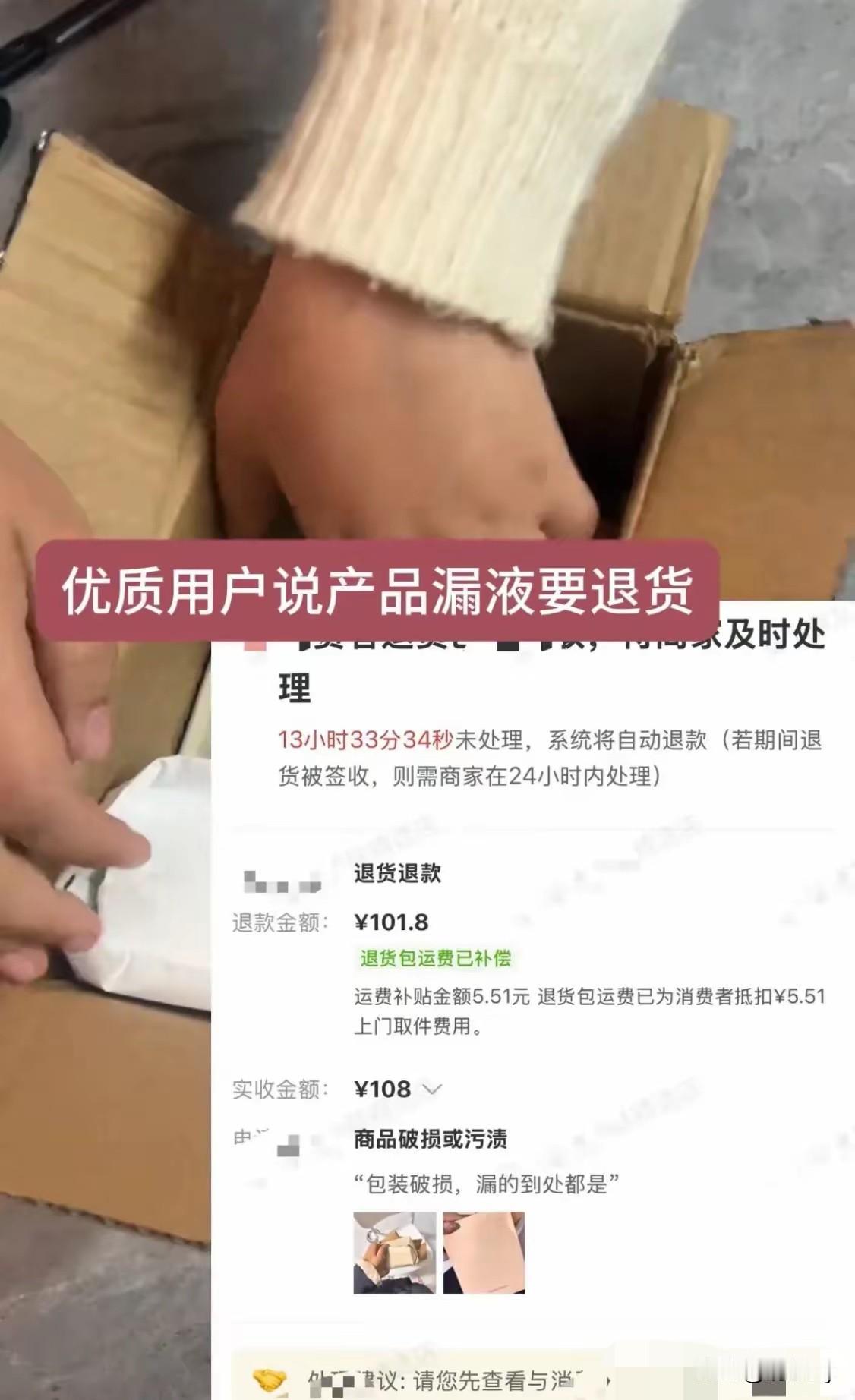转自:蚌埠新闻网

蚌埠发布客户端讯(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立春文/图)11月9日下午3点22分,蚌埠人丁洪生抵达了此行的终点——蚌埠火车站,为他1500多公里的返乡徒步旅程画上句号。找了个擦鞋凳坐下,他说“实在有点走累了”,此刻最想做的是唱一首《故乡的云》。
这句想唱的歌,为他49天的返乡徒步画上了一个注脚。从9月21日下午出发,到11月9日抵达,丁洪生用双脚丈量了从深圳到蚌埠的距离。其间因台风有一天被困在宾馆,实际行走49整天。
他说,这是一次挑战,一次记录,也是一次回归。

一个“说走就走”的决定
徒步的念头,源于一个短视频。
“刷到湖南一个爸爸,带着儿女从深圳走了800公里回家。我想,小孩都能走,我一个大人走1500公里,应该也能完成。”这个想法一出现,丁洪生便决定付诸行动。他曾问过自己的孩子是否愿意同行,孩子因觉得“累”拒绝了。
“他不干,我自己干。”丁洪生的性格里,有一种“说干就干”的劲头。他自称“丁哥爱折腾”。1992年,初中毕业的丁洪生去深圳打工,开过饭店,还办过旅游公司、布料公司和服装公司。
这种行事风格,贯穿了这次徒步的全过程。“我没有攻略,就是手机导航一开,导到蚌埠市,三百多个小时,就照着走了。”
徒步,也是为了记录。丁洪生从出发第一天起,就用视频记录全程并上传到个人社交平台。“核心目的就是把素材集中起来,等我老的时候看,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回忆。也是对孩子的一种软性教育。”
他说,做这件事,还因为少有人做。“如果所有人都走,我就不走了。就是因为没有人走,这个意义就很大。”

一段“稀里糊涂走”的旅程
没有攻略的徒步,意味着未知和困难。丁洪生回忆,手机导航经常把他引向“稀奇古怪的山间小路”,这些路占了全程近一半。
“走小路,吃住不好解决。”他有时只能在村里的小店买泡面和水。下午三点,他发现距离下一个能住宿的镇子还有二十多公里,只能继续走,最长的一天走了超过50公里,“光走都走十几个小时。”
出发前,他最担心两件事:车祸和脚起泡。
他认为,徒步最大的危险来自车辆。许多乡道和山路路面狭窄,“你只能踩着白线走,大货车就从旁边贴着你过”。为安全起见,他必须迎着车流走,因为背对车辆时,司机右侧存在盲区,危险性更高。夜间行走时,他会用小手电筒晃动以提醒来车。
身体的挑战从第五天就开始了。那天,他的脚趾磨出了水泡。“以前也有过,拿针捅破,把水放掉,贴个创可贴就行了。”但问题在于,这次他不能停下来休息。最终,他依靠晚上休息时让伤口自然风干和吸收来恢复,脚上也留下了疤和老茧。
路上最严重的一次受伤,是在江西省新干县。“当时我急行军,一个虫子咬了腿一下,整个地方都肿了,捏都捏不动,像石头一样。”他起初以为是肌肉拉伤,后来路上的村民告诉他,这是被毒虫咬的。他没有去看医生,就那样一瘸一拐地坚持走,直到终点。
背包出发时称重32斤。里面有几件换洗衣物、一双雨鞋,还有一个帐篷。帐篷是他为应对极端情况准备的,他设想过如果找不到住处,就去村委会求助搭帐篷,但“这个场景没有存在”,他凭体力坚持到了每一个能住宿的镇子。
49天的风餐露宿,最终在11月9日上午抵达蚌埠与凤阳交界处时,迎来了情感的顶点。“我进了蚌埠就算成功了。”在距离市界还有三公里时,情绪就已经涌了上来,回忆起路上的种种不易和危险,他流泪了。

一个“有始有终”的旅程
丁洪生为这次徒步的起点和终点,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起点,定在他1992年初到深圳时第一个工作的地方——蛇口。“我当时从蚌埠去深圳,就是从蚌埠站走的。现在我从深圳第一个工作点出发,回到蚌埠站,我觉得这有始有终,是一个人生的闭环,就相当于我已经退休了,回家乡了。”
终点的选择,是在他进入安徽省后才最终确定的。他曾想过市政府、万达广场,最后还是选了火车站。“我家就在旁边,意义更大。”因为家人大多居住在合肥,曾有人建议他可以在合肥结束行程,他拒绝了。“我是出生在蚌埠,长大在蚌埠。到蚌埠才是我真正的情怀,真正的根。”
一路走来,他对家乡蚌埠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观察。“蚌埠我感觉一直是管理的很好,”他说,“尤其从卫生、交通的管理和人员素质方面,对蚌埠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还是挺满意的。”
接下来的几天,他打算在蚌埠休息,看看朋友,去淮河边走走,也去看看自己的母校。“给身边的粉丝网友介绍一下我们蚌埠的美景美食。”
之后,他将返回深圳,继续他“爱折腾”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