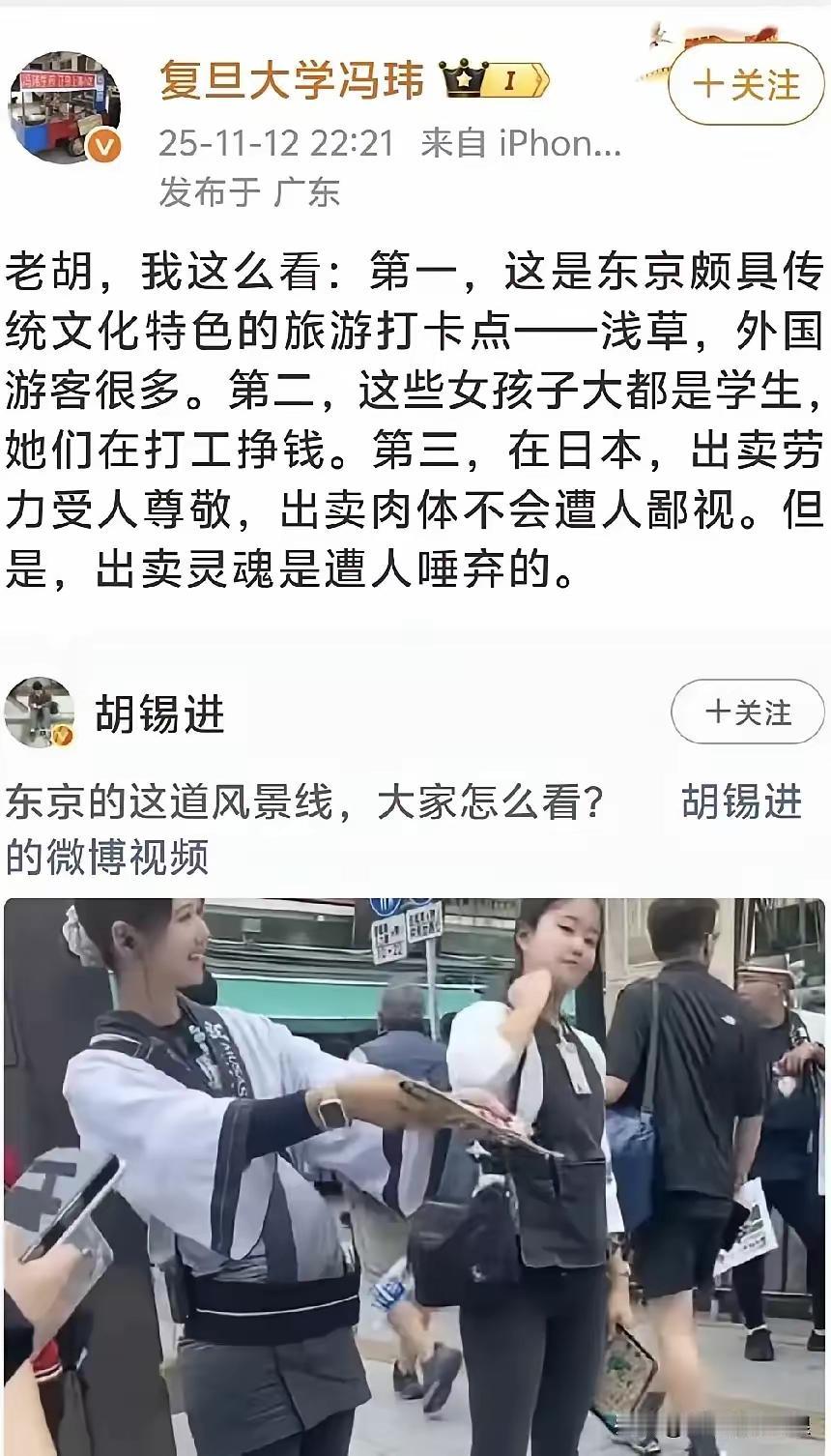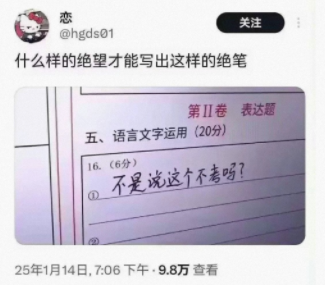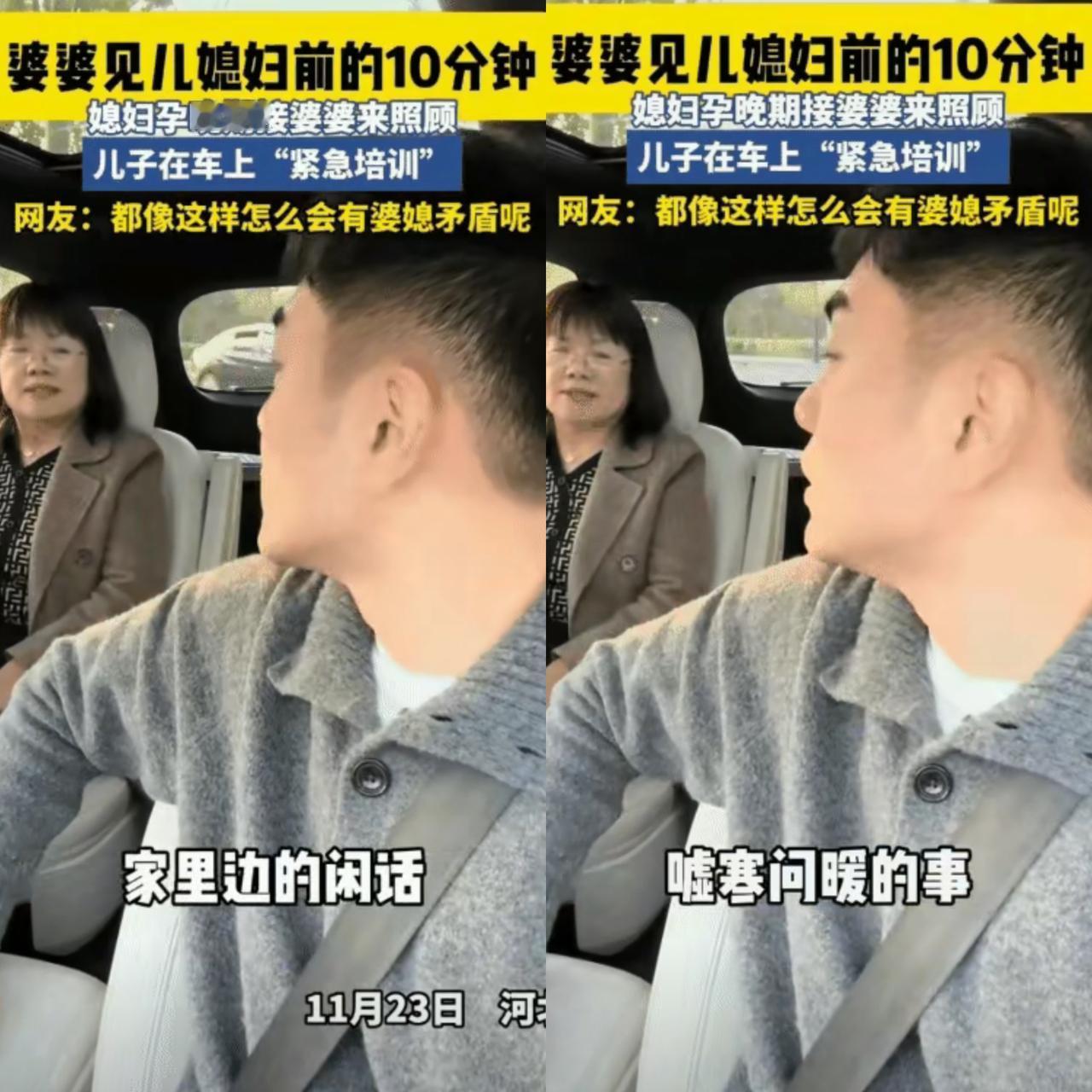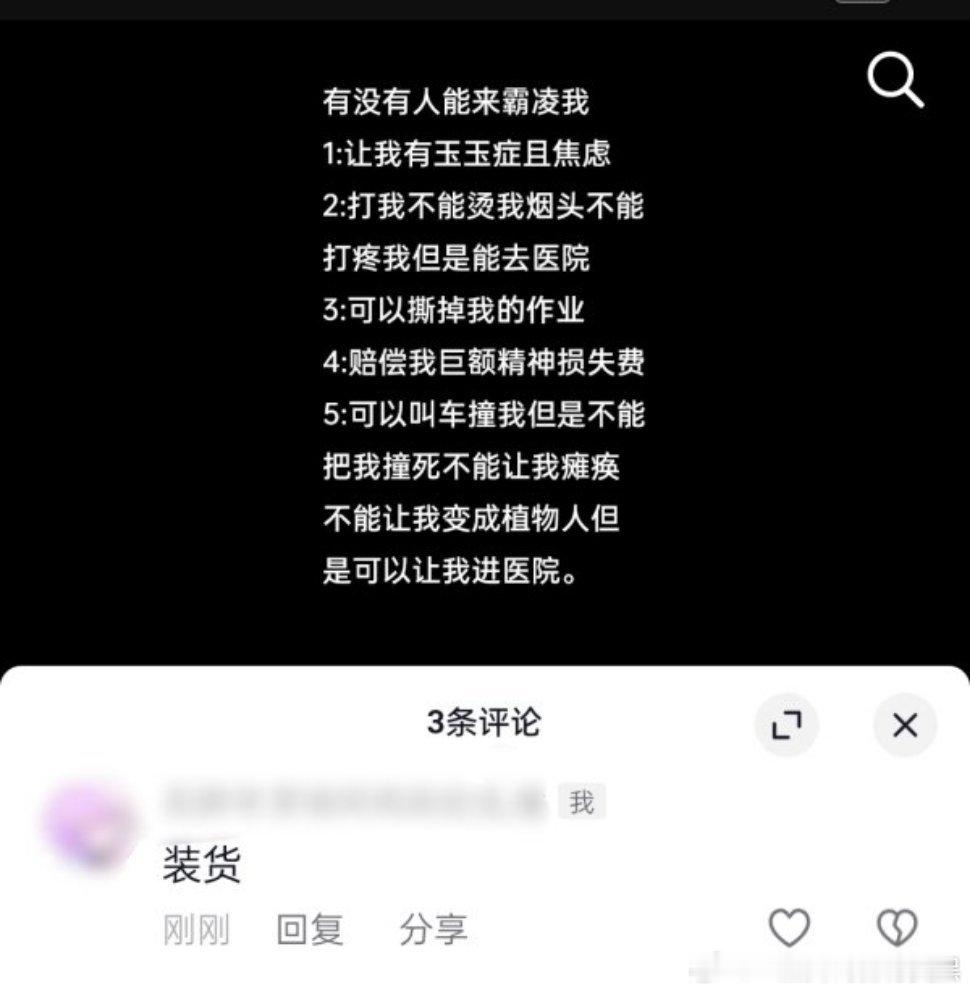一天,茅以升和妻子手挽手在公园里散步,聊到感情问题时,妻子说:有些第三者挺可怜的,被男人骗、又被抛弃!茅以升听完愣在那,然后小声的对妻子说:对不起,我外面有人了,可我没想抛弃她,把她接来行吗? 要说茅以升不爱他的原配戴传蕙,那绝对是瞎说。他们的故事,开头比很多偶像剧都甜。 那会儿还是包办婚姻的年代,但茅以升对戴传蕙,那是一见钟情。戴传蕙比他大一岁,长得漂亮,知书达理,是标准的大户人家闺秀。茅以升第一次见她,回去就跟他爹妈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俩人结婚后,茅以升亲昵地喊她“蕙君”,还送了本《浮生六记》当定情信物,把她比作书里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芸娘。 婚后,戴传蕙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家里家外操持得井井有条。茅以升要去美国留学深造,一走就是好几年。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拖着孩子,在夫家过日子,多难啊。可戴传蕙毫无怨言,她懂丈夫的抱负。两人靠着一封封跨越太平洋的信件,维系着感情。茅以升把妻子的照片放在钱包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这是他艰苦求学时最大的慰藉。 可以说,没有戴传蕙这个稳固的大后方,就不会有后来功成名就的茅以升。 她是他事业的基石,也是他曾经全部的情感寄托。 可人呐,是会变的。尤其是当生活开始变得动荡,人心也就跟着摇晃了。茅以升回国后,事业蒸蒸日上,但也越来越忙。他常年扑在桥梁工地上,一年搬一次家是常事。家庭的重担,六个孩子的教养,几乎全压在戴传蕙一个人身上。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压力,让戴传蕙的身体垮了,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后来甚至发展成了抑郁症。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权桂云,出现在了茅以升的生活里。 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那年他50岁,功成名就。而权桂云,才20出头,是个家境贫寒、性格怯懦的苏州姑娘。茅以升出于同情帮了她一把,一来二去,这种“同情”就变了味。 一个是在病痛中日渐憔悴的结发妻子,一个是年轻脆弱、对他满眼崇拜的红颜知己。茅以升没能守住底线。他和权桂云同居了,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茅玉麟。 这事儿最让人唏嘘的是,茅以升试图“两全”。 他一边偷偷照顾着权桂云母女,一边也尽心尽力地对待家里的戴传蕙,甚至因为愧疚,对妻子更加关心。而戴传蕙对丈夫是百分百的信任,她曾对人说:“跟着他,我放心,他心里只有工作,不会沾花惹草的。” 这种信任,在茅以升坦白的那一刻,碎得有多彻底,可想而知。 坦白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忠诚老实运动”背景下,组织要求每个人都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和家庭关系。茅以升躲不过去了。当他说出一切后,戴传蕙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呆呆地坐了很久,最后长叹一声:“算了,他也不容易。” 一个女人的心,得有多宽,才能说出这句话?她甚至在茅以升保证不再见面,但每月给权桂云母女寄生活费时,还叮嘱他:“多寄一些,别亏待了孩子。” 戴传蕙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大度”,维持着这个家的表面和平。但谁都知道,心里的那座桥,已经塌了。1967年,常年被抑郁症折磨的戴传蕙去世了。 她走了,茅以升觉得,自己欠权桂云的,该还了。他不顾子女们的激烈反对,把权桂云母女接回了家。他想给她们一个名分,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可他忘了,这个家里,还有六个长大了的、爱着母亲的孩子。 茅以升的长子茅于越,当时在瑞典工作,是父亲最器重的儿子。听闻父亲的决定,他直接放话:“家里有她没我!” 这句话,成了茅家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茅以升的其他几个子女,也用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态度:纷纷离家,远赴海外,跟父亲断了联系。他们无法原谅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更无法接受那个“第三者”登堂入室。 权桂云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好过。她在这个家里,活得小心翼翼,像个外人。她包揽了所有家务,省吃俭用,连件新棉袄都舍不得做。每次茅家的孩子回来看望,她就自觉带着女儿躲出去,等人家走了再回来。 她以为用隐忍和退让,能换来一丝接纳。可她错了。孩子们心里的那根刺,早就扎深了。在这个家里待了仅仅八年,权桂云也因为长期心情郁结,早早地抑郁离世了,年仅50岁。 两个女人,都因他而陷入悲剧。而茅以升自己,也终于迎来了他最凄凉的晚年。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身边只有小女儿茅玉麟照顾。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脑子糊涂了,却唯独记得一件事,嘴里总是念叨着:“蕙君,我对不起你……” 他想念远在海外的六个子女,不停地给长子茅于越写信,盼着回信。可两年,一封都没有。 1989年,94岁的茅以升在北京协和医院弥留之际,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大儿子一面。可茅于越,终究没有回来。为了让老人安心闭眼,小女儿茅玉麟模仿哥哥的笔迹,给他写了一封“原谅信”。 据说,这位为中国建了一辈子桥梁的巨匠,在看到那封伪造的信后,手里紧紧攥着它,眼里流下一行泪,才缓缓咽下了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