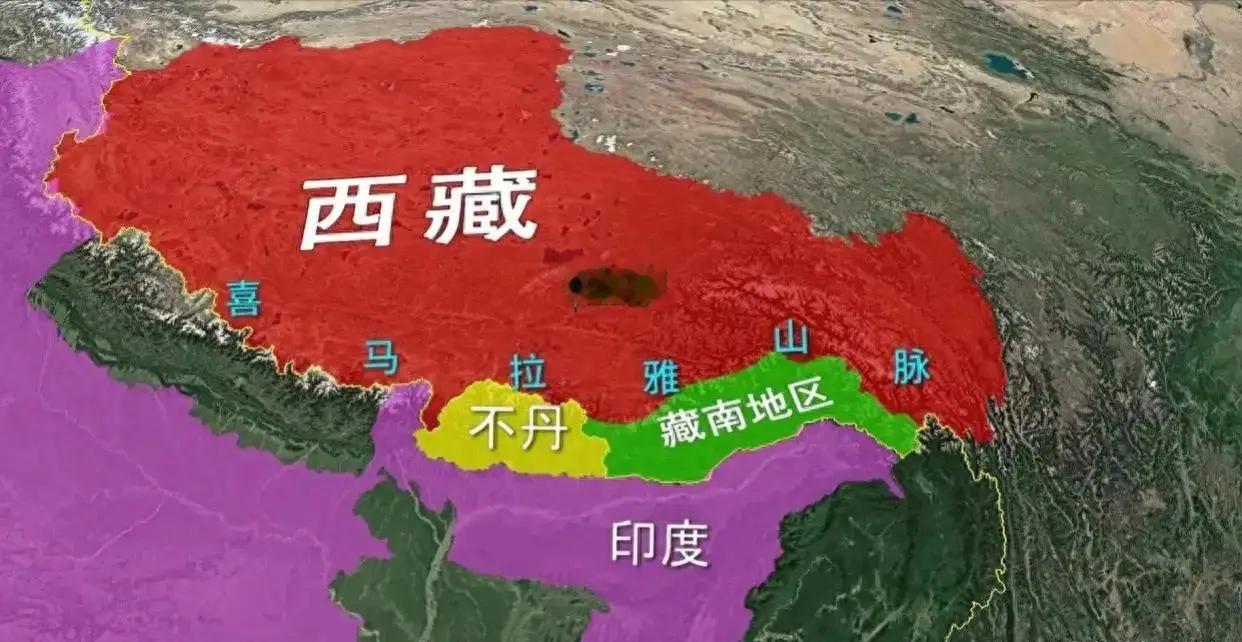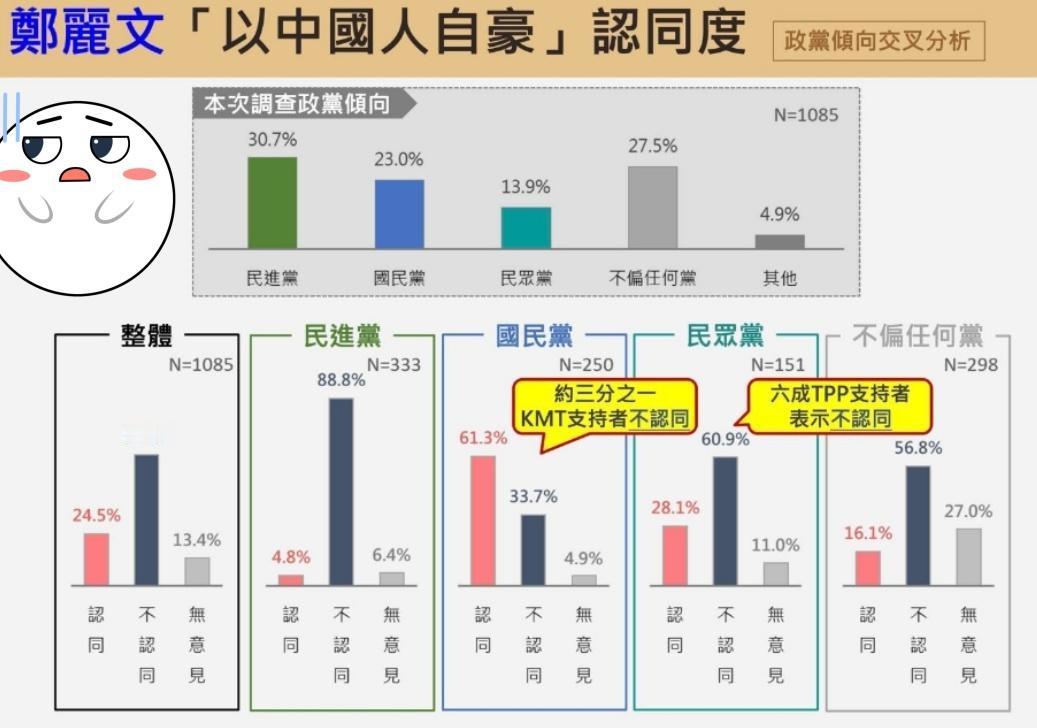【民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吗?孙玉良: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民主土壤】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将“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多党竞争、普选制等形式紧密捆绑,仿佛民主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专利”。然而,细究历史与理论,这种论断实乃一个需要被澄清的迷思。民主,绝非资本主义的专属品;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为民主提供了更为深厚和真实的土壤。
关于“民主”与制度的关系,袁大成兄对我多有教益。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概念范畴。民主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内的概念,核心在于“人民的统治”,关乎权力归属与行使方式。而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内的概念,其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将政治领域的民主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制度强行捆绑,在学术上是一种混淆。如果一定要探讨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关联性,我们会发现,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联系更为紧密和内在,公有制是培育民主公共精神的天然沃土。
民主的真谛,并不仅仅在于投票的瞬间,更在于一种持续存在的、关注公共事务的“公共精神”。这种精神是民主政治的灵魂。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发展、集体的福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利益关联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关心“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如何。政府的一项政策、企业的一次决策,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攸关”的机制,必然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监督政府行为的巨大热情和内在动力。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民众的民主热情空前高涨,正是因为大家意识到国家的公共事务就是自己的事务,从而“不得不关注政府干得怎么样”。
反观漫长的私有制历史,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氛围中,经济利益高度原子化,人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自己的私产,对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事务往往缺乏持久的关注动力。这正是中国几千年私有制历史未能自发产生现代民主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需要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关怀,而纯粹的私有制恰恰在结构上削弱了这种关怀的普遍性基础。将视野放宽至全球,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史,也并非资产阶级独角戏,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角色。
诚然,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王权的斗争中,追求并确立了“宪政”原则,其核心如三权分立,最初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皇权(尤其是随意征税的权力),以保护私有产权和商业利益。宪政解决了“权力不能任性”的问题,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权在民”的民主。
现代民主的标志——普选制,其实现路径充满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烙印。在欧美历史上,普选权的扩大(从有产白人男性到无产者、到女性、到少数族裔),并非统治阶层的恩赐,而大多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左翼力量及广大民众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争取来的。资产阶级在初期往往对普选权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广泛的民主会危及其财产权和统治地位。正是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冲击着原有的权力结构,将“民主”从少数人的特权,真正推向广大人民。无论是欧洲的普选制民主,还是美洲的普选制民主,其实现历程都深刻烙印着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与力量。
将民主视为资本主义专利的观点,既在理论上混淆了政治与经济的范畴,也在历史上遮蔽了社会主义运动对于民主实现的决定性贡献。民主的根基在于“天下为公”的公共精神,而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将社会成员的利益紧密联结,为这种精神的生发提供了最适宜的经济基础。西方的民主实践史也告诉我们,正是追求社会公平与大众参与的社会主义力量,将民主从形式的宪政框架,填充进了实质的人民权利。
因此,答案已然清晰: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在追求更广泛、更真实、更实质的人民民主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非但不缺席,反而因其与生俱来的公共属性,展现出更为广阔和深厚的民主土壤与潜力。在社会主义国家讲民主应该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不讲民主了,那当谁的家、作谁的主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民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此,堂堂正正地讲民主,践行民主,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义务。视民主为“毒蛇猛兽”,反而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