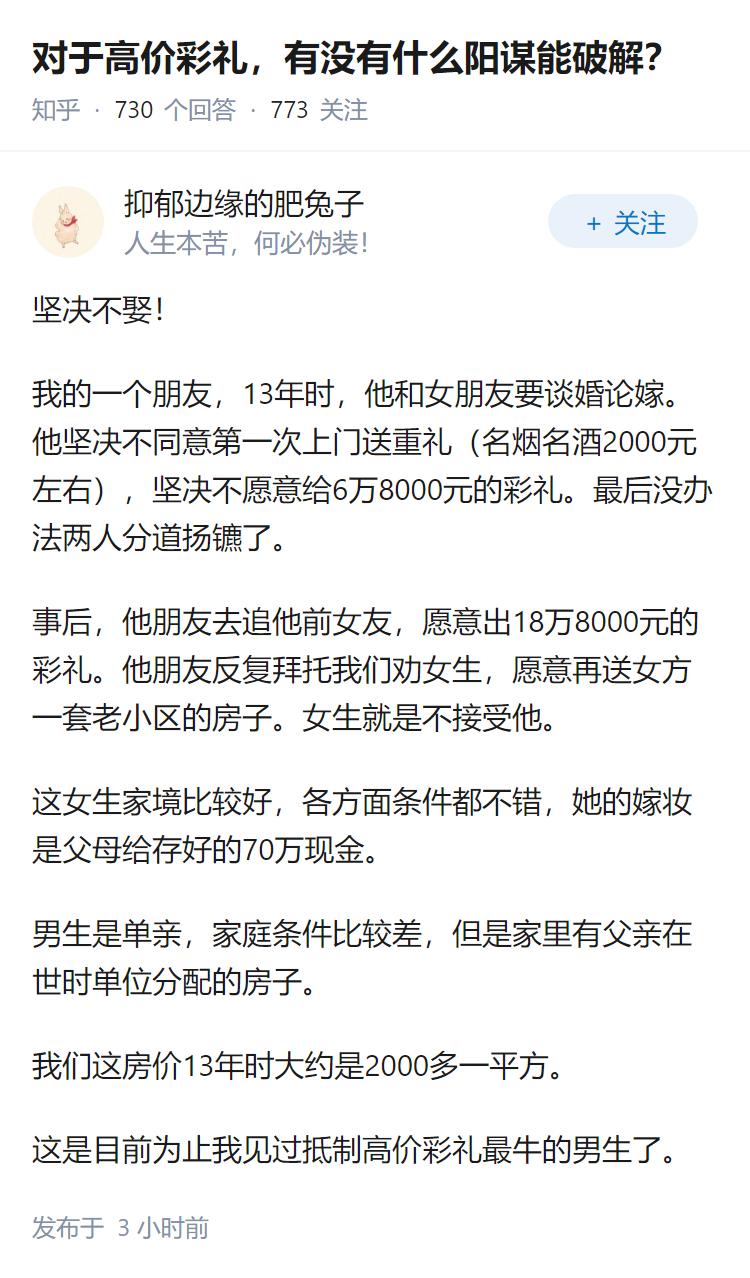《螺壳里的绣针》 入秋的雨裹着腥气,青溪村的溪滩浮着死鱼。阿生扛着破渔网往家走时,踢到个硌脚的硬物——是只巴掌大的田螺,螺壳泛着暗银,纹路像被血浸过的绣线,在雨里黏着他的裤脚。 他把田螺扔进木盆时,盆沿忽然裂了道缝。阿生没当回事,他家的旧物总这样:灶房的陶釜缺了口,床板钉着锈钉,连窗纸都破着洞,漏进的风裹着邻村的闲话——上个月村里的织锦匠突然投了溪,尸身捞上来时,指缝里夹着片银线。 第二日清晨,阿生是被血腥味呛醒的。灶台上摆着热粥,碟子里的鱼煎得焦黑,鱼眼却翻着白,像极了溪滩上的死鱼。更怪的是,他破了洞的渔网被补得密不透风,网眼里缠着根银线,线尖沾着暗红的痂。 “谁?”阿生攥着柴刀撞开灶房的门,只有木盆里的田螺浮在水面,螺壳的纹路正慢慢变红。 接连三日,灶房的饭香总裹着腥气。第四日,阿生假装扛着渔网出门,却躲在柴垛后——辰时刚过,田螺的壳“咔”地裂开,溢出的光裹着个穿月白衫的姑娘,指尖拈着银线,正往他的旧衣上绣纹。可那纹样不是云纹,是缠在骨头上的锁链,线尖还滴着暗红的水。 “你绣的是什么?”阿生的柴刀掉在地上,姑娘的肩猛地颤了,银线“唰”地缠上他的手腕——线尖冰凉,像死人的指节。 “三百年前,我是织锦坊的绣娘。”姑娘的声音发着颤,螺壳在她脚边渗出血珠,“宫里要我织‘锁魂锦’,说要钉住叛军的魂魄。可那锦缎要用活人的血浸线,我偷偷换了棉线,被绣坊主扔进青溪,螺壳里嵌着他的绣针——那针上,还缠着三十个绣工的魂。” 阿生的手腕起了红痕,像被针划过。他忽然想起邻村织锦匠的死:那人死前说“灶房有银线”,尸身的指缝里,正是这沾血的线。 “你是在找替死鬼?”阿生往后退,姑娘却突然跪下去,螺壳裂得更开,露出里面嵌着的锈针——针尾刻着“织锦坊”三个字,正是三百年前的旧物。 “那绣针要吸够三十一个魂才能碎。”姑娘的衫子渗出血印,“前三十个,都是碰过这螺壳的织匠。你是第三十一个,可我看你把螺壳揣在怀里暖着……不想你死。” 阿生的后背贴着凉墙,灶房的陶釜突然“砰”地裂了,里面滚出半只绣鞋——是邻村织锦匠的,鞋尖缠着银线。 这时,院门外传来村老的敲锣声:“阿生家藏了妖物!那织锦匠的魂,定是被他勾走的!” 阿生攥住姑娘的手腕:“怎么毁了这针?” “用织匠的血浸的针,得用真心护过它的人的血融。”姑娘的指尖按上他的手腕红痕,“你把螺壳揣在怀里时,体温已经裹住了针魂——只要你把血滴在针上,我和那三十个魂,就能散了。” 院门被撞开时,阿生攥着锈针往手腕划去——血滴在针上的瞬间,螺壳突然炸开,银线裹着三十道虚影往溪里飘,姑娘的衫子化作片云纹锦,落在他的掌心。 村老们举着火把冲进来时,只看见阿生攥着片锦帕,灶房的木盆裂成了碎块。 后来阿生再没碰过织锦,只靠着打渔过活。他的渔网总缠着银线,网起的鱼总带着云纹般的鳞。有人说他被妖物缠了身,可阿生摸着锦帕上的锁链纹笑:“那不是锁链,是绣针断时,她替我绣的平安结。” 只是每逢雨天,青溪的水会泛着银线,有人说那是没散干净的魂,也有人说,是绣娘的针还在缠着重生的路。 螺丝田螺 凤凰田螺 阿 绣 钉螺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