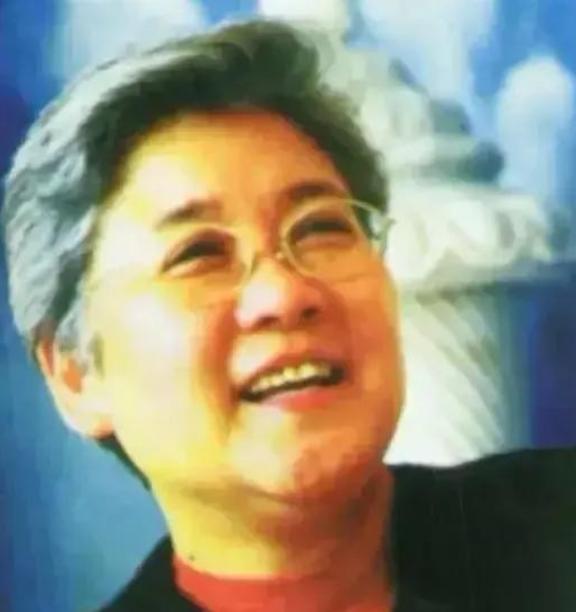1977年9月,唐闻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从此她远离了工作多年的外交系统,几年以后,她被分配到中国日报社工作,此后又在铁道部长期任职。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7年9月,34岁的唐闻生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外交部的办公楼,这个曾经为基辛格和尼克松担任翻译、被外国媒体称为“能赢得三个州”的外交明星,即将前往河北的五七干校,开始她完全陌生的劳动生活。 从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到乡村的田间地头,这个落差大得让人难以想象,几年前,她还穿着得体的制服站在周总理身后,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每一句话精准地传递给对方。 那些照片被各国报纸反复刊登,她冷静专业的神态成为中国外交形象的一部分,可现在,她要学着挑水、插秧、割麦子,手上磨出了从未有过的老茧。 干校的日子简单而重复,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大家下地干活,她不是没有过抱怨的时刻,毕竟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身体和心理都需要巨大的调整。 但时间久了,她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晚上回到宿舍,她偶尔还会翻翻随身带的英文书,但更多时候是直接倒头就睡,那些国际会议、外交辞令、同声传译,仿佛都是上辈子的事了。 1978年底,干校生活结束,她回到北京,却没有回到外交部,组织上的安排是让她去中共中央党校进修几个月,之后分配到了刚筹备创刊的《中国日报》。 这是一份面向国外读者的英文报纸,需要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的人来把关,唐闻生到任后发现,这里的工作方式跟外交部完全不同。 外交讲究的是精准传达,不能有半点偏差;办报纸则需要考虑可读性、传播效果,还要让外国人看得懂、愿意看。 她开始逐篇审稿,用红笔圈出那些翻译腔严重的句子,跟年轻编辑们讨论怎么表达更地道,有时候为了一个词的翻译,她能跟作者争论半天,报纸创刊初期困难很多,从版面设计到内容选择都在摸索。 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国际交流经验用在这里,慢慢帮《中国日报》建立起一套更符合国际阅读习惯的编辑体系,这份工作没有外交部那么光鲜,但她做得认真投入。 就在大家以为她会在报社一直干下去的时候,1986年又来了新的调动,这次是铁道部外事局局长,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从新闻到铁路,跨度实在太大。 但当时中国铁路正处在大发展时期,需要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急需既懂外语又有国际谈判经验的人,唐闻生去了,从零开始学铁路知识。 她跟着工程队去工地,拿着小本子记下那些专业术语,线路规划、车体参数、信号系统,这些东西比外交辞令复杂得多,有一次在西南勘察线路,她脚踝扭伤了还坚持走完全程,回到驻地时脚肿得厉害。 同事们都说这个从外交部来的女局长,干起活来比男人还拼,她在铁道部一干就是十几年,参与推动了不少国际合作项目,直到1999年退休。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外交天才会在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候被下放,之后又辗转报社和铁道部,再也没回到外交系统。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个年代的个人命运,从来不完全由自己决定,她经历的起伏,是时代给无数人留下的共同印记。 但真正让人佩服的,不是她曾经站在多高的位置,而是她在每一次转折后都能重新站稳,从外交官到农民,从编辑到铁路干部,她没有抱怨,也没有放弃。 每到一个新岗位,就踏踏实实从头学起,把事情做好,这种韧性,比任何头衔都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分量。 2024年,81岁的唐闻生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站在领奖台上,她依然是那副平静的样子。 她这一生翻译过的,不只是语言,还有命运的每一次转折,那些年的沉浮教会她,人生没有固定剧本,能做的就是接受变化,然后继续往前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独家专访:唐闻生印象——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