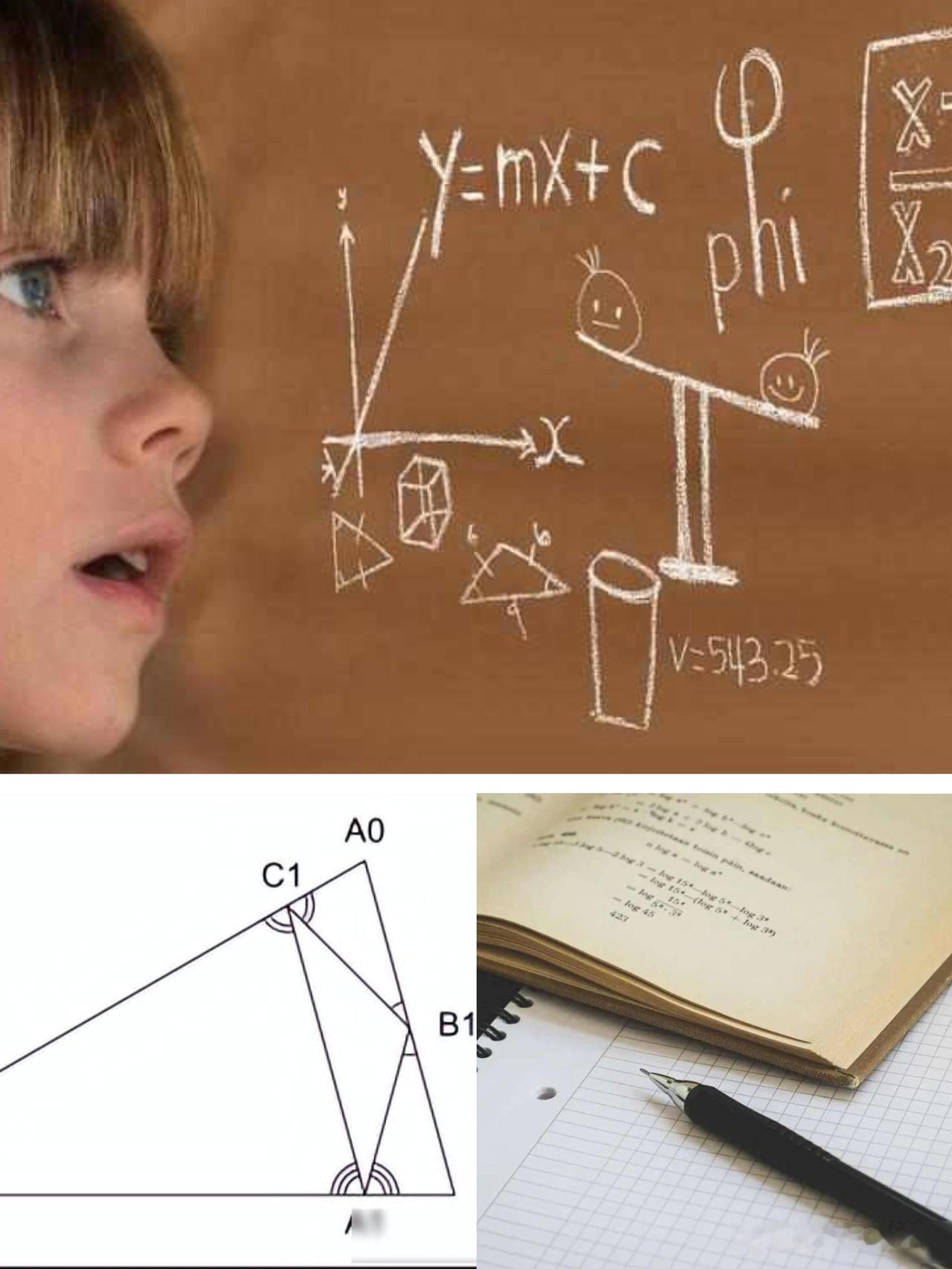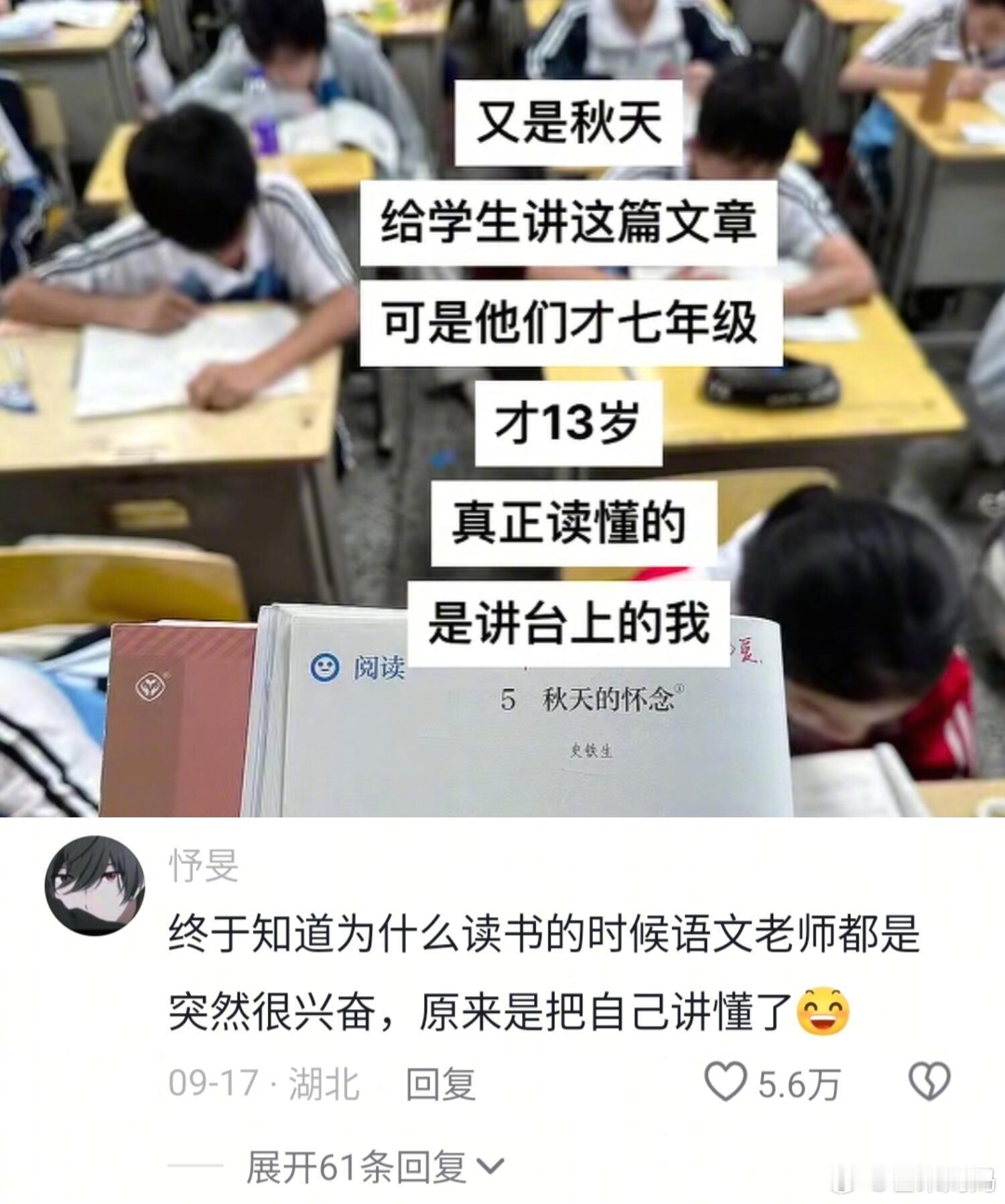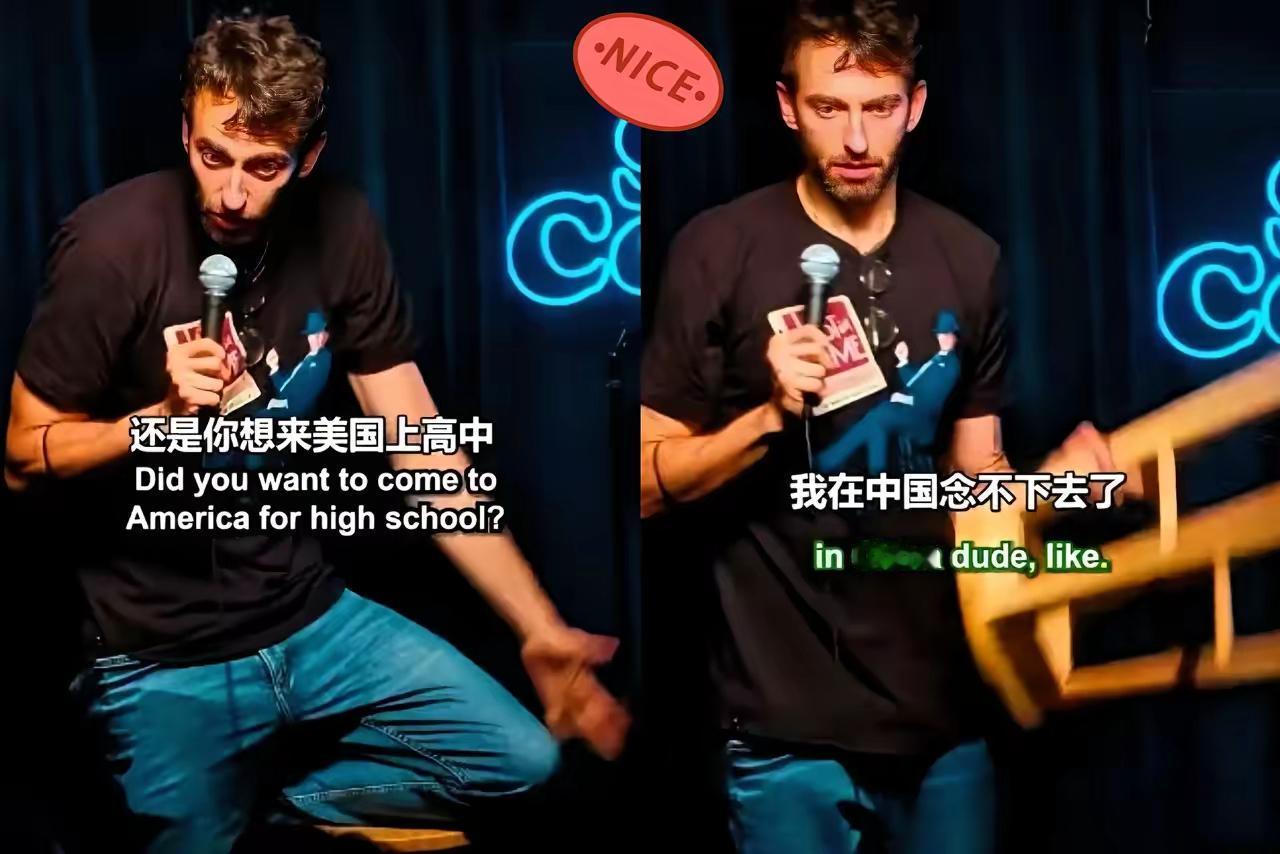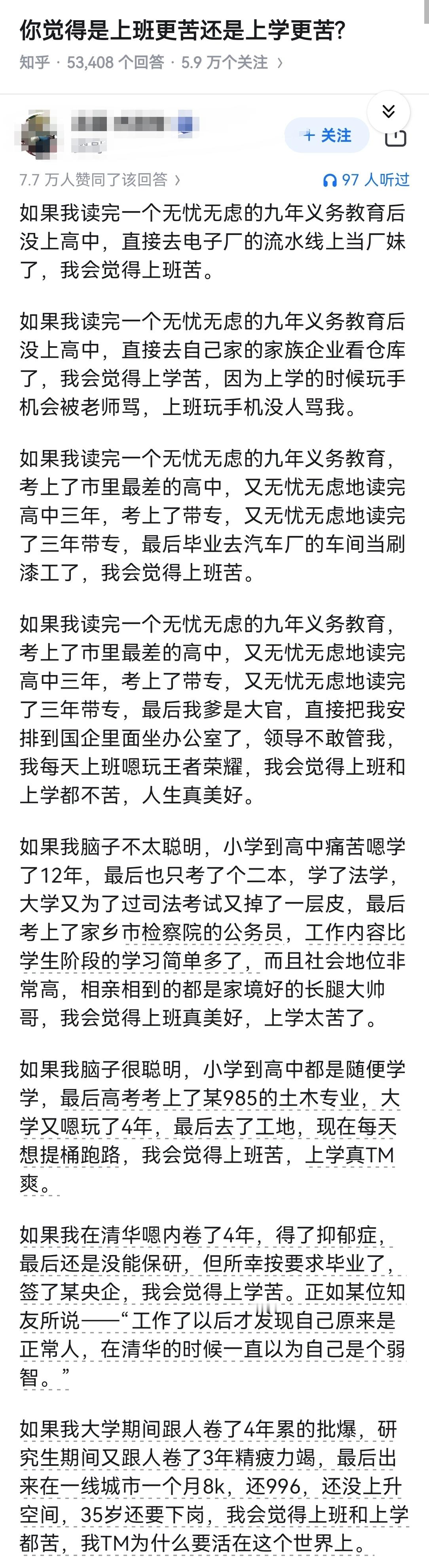施一公再次语出惊人!他说:“美国科学的强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仅没有衰退,还会在今后几十年内,引领世界的发展!”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美教育的差异:“我们的教育,太过于抑制学生的创新能力!”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施一公说美国科学会继续引领世界几十年,这话听着扎心,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他浸在美国科研圈近二十年后的大实话。 他可不是光看表面,而是从课堂到实验室,从人才培养到成果转化,实打实摸透了其中的门道,核心就落在了“教育养不养得出创新的种子”这件事上。 他在普林斯顿做研究时发现,美国的实验室从来不怕“走弯路”,有次他的博士后导师带学生做结构生物学研究,一个博士生花了八个月验证一个假设,最后全是负面结果——也就是实验根本达不到预期。 换咱们这儿,学生可能早慌了,老师也得催着换课题,但那位美国导师反而夸这学生“做得漂亮”,说这些可靠的负面结果直接排除了一条错路,比瞎猫碰死耗子强多了。 施一公后来总跟自己的学生说,科研的本质就是试错,可咱们的教育从小就教孩子“别犯错”,考试要标准答案,作业要按套路来,久而久之,谁还敢瞎琢磨? 课堂上的差别更明显,美国学生上课坐得歪歪扭扭,却敢当着教授的面拍桌子质疑观点;咱们的课堂规规矩矩,学生都习惯了“老师讲、记笔记”,偶尔有提问的,也多是问“这题怎么答”,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要这么答”。 施一公刚到美国读博时,生物课逻辑跟不上,差点不及格,全靠应试教育打下的数理基础撑着。 但他很快发现,美国同学虽然基础不如他扎实,却敢想敢问,比如学基因编辑时,有人直接跟教授争论“会不会有伦理风险”,有人琢磨“能不能换个更高效的酶”,这种追问的习惯,恰恰是创新的起点。 再看人才选拔,这更是戳中了咱们的痛点,施一公总说,咱们的教育是“均值很高,方差很小”,意思是学生平均分能甩别人一截,但最拔尖的和普通优秀的拉不开差距。就像高考,就算你数学能考满分,英语差几分也可能落榜。多少偏科的“怪才”,因为总分不够被挡在好大学门外? 可美国的SAT成绩在录取里占比远没高考那么重,学校更看重学生的科研经历、创意想法,甚至是独特的兴趣爱好。 马斯克年轻时天天琢磨火箭,乔布斯辍学去学书法,换在咱们这儿,大概率会被当成“不务正业”,可正是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成了改变世界的科技巨头。 有人说咱们的孩子补课多、做题勤,怎么还比不过美国学生?施一公的答案很实在:科技突破靠的是顶尖天才,不是大批中等优秀的人。 美国每年可能就几百个“120分”的天才冒出来,咱们每年上百万考90分的学生,却出不了几个能捅破科技天花板的人。 这不是说咱们的孩子不聪明,而是教育把他们的“棱角”磨平了,学校管得太细,坐姿、发言都有规矩;考试卡得太死,一分定生死,结果是听话的孩子不吃亏,有个性的孩子难出头。 更关键的是,美国的教育能和科研、产业拧成一股绳,施一公观察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技术创新与伙伴局,把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和企业的需求直接对接,就算是学生的奇思妙想,也能拿到资金支持变成产品。 反观咱们,不少高校的研究还停留在“发论文”上,学生就算有好想法,要么缺资金,要么缺渠道,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这背后还是教育理念的差距——美国教学生“怎么把想法变成现实”,咱们更多教“怎么把知识记牢固”。 当然,施一公从没否定过咱们的教育,他自己就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数理基础打得牢,才让他在美国扛过了最初的难关。 但他更着急的是,应试教育带来的“求稳思维”正在拖创新的后腿,犹太裔科学家总爱选最冒险的研究方向,咱们的科学家大多选稳妥的课题,不是能力不够,是怕失败、怕出错,这种心态从小就被教育种下了。 不过也不用灰心,施一公回来办西湖大学,不就是想改这个现状吗?新高考也开始尝试多元录取,不唯总分论了。 说到底,承认差距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要明白:教育不是批量生产“高分学生”,而是要给每个孩子的创新留块自留地。 什么时候咱们的课堂敢让学生“抬杠”,实验室敢让学生“试错”,选拔时敢给“怪才”机会,咱们的科技才能真正拔尖,这才是施一公说这话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