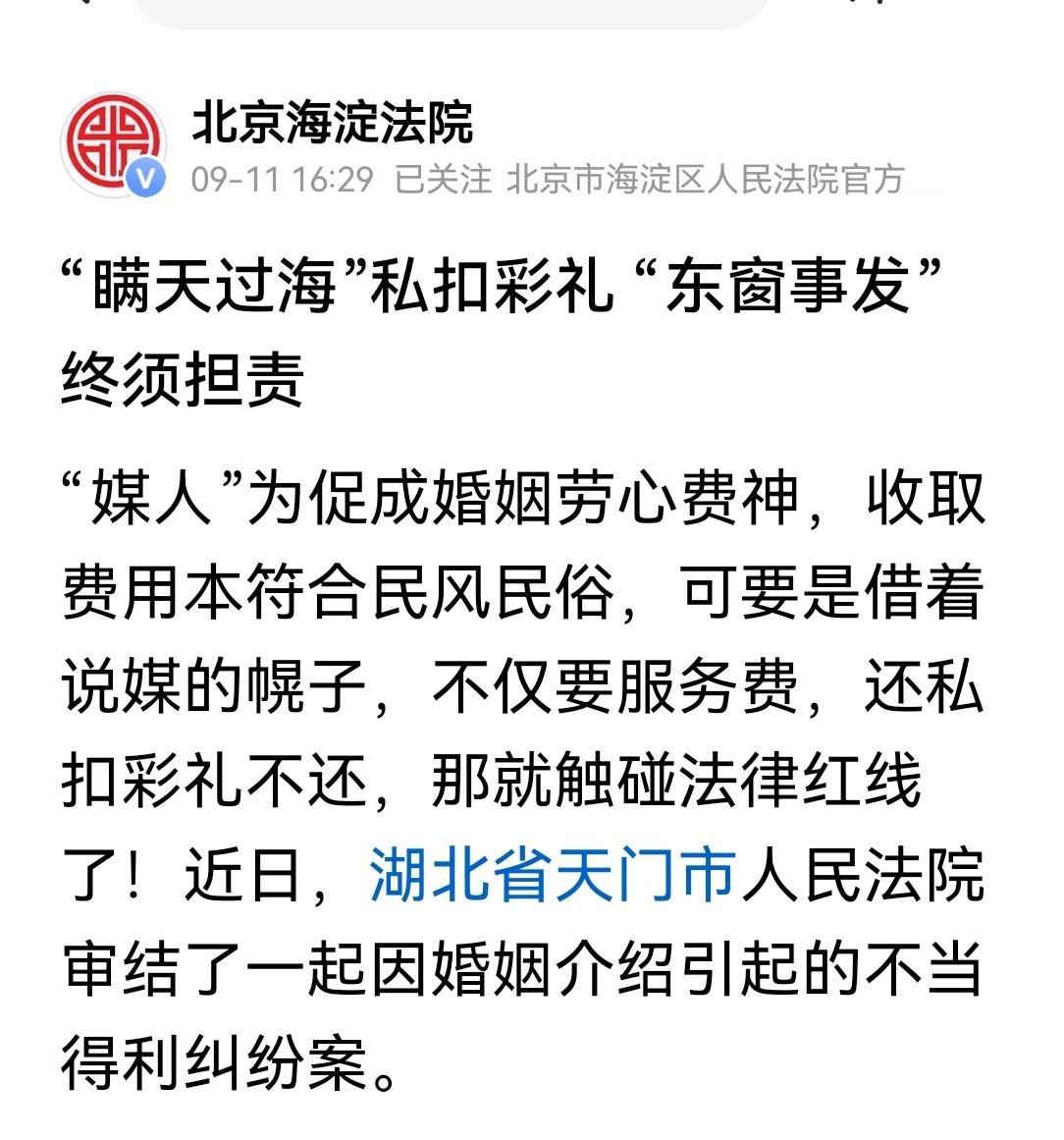湖北天门,小王三十多岁还没对象,父亲老王急得团团转,眼看同龄人都抱上了孙子,家里却冷冷清清。有人介绍说有个媒人李某,专门跑外地牵线,只要花钱就能找到媳妇。老王当时觉得,这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李某给小王介绍了一个外地女子,双方谈婚论嫁,老王给了20万彩礼,结果李某拿走12万,只给了对方8万。老王得知后非常愤怒,将李某告上法院。 老王眼看儿子小王30多了,都没有对象,非常着急。要知道像他这个年龄的孙子都十几岁了,但小王现在连有人介绍都没有。2018年9月,老王找到媒人李某,当面承诺:只要能让儿子领证结婚并生活在一起,就给5万元介绍费。在农村,这可不是小数目,但老王认了。没想到李某很快就联系上,说找到一个外地姑娘小兰,她和家人都同意,但前提是要收20万元彩礼。 老王一听,立刻让小王把钱转给李某,由他转交。几天后,小王就见到了小兰,俩人相处得还算融洽,很快就把小兰带回了家。小王也兑现承诺,直接给了李某3万元介绍费,剩下的2万元约定等结婚后再支付。 日子一切顺利。小兰住进小王家,长辈们也都挺满意,不久便领了结婚证,还办了酒席。就在新婚不久的一天,小夫妻闲聊时,小兰随口说起,她家当初收到的彩礼其实只有8万元。小王愣住了,他明明亲手给了李某20万,怎么到了女方家只剩下8万? 小兰再三确认,她家确实只收了8万。小王当时就火冒三丈,当面质问李某。李某抵赖不下,只能承认,当初看到小王在外打工多年,手里宽裕,就起了贪念,把12万元据为己有。本来以为能糊弄过去,没想到被拆穿。 小王要求立刻退钱,李某却推三阻四。一会儿说小王还差他2万元介绍费,一会儿又说那12万是“小王自愿给的谢媒礼”。从2018年到2025年,七年时间,小王追讨无果。最终,他在2025年7月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返还1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不具备婚姻介绍合法资质,收取费用本身就存在问题。他受托代交20万彩礼,却只交付8万,私吞12万,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返还。因此,小王有权要求李某返还。 另外,按照《民法典》第922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小王把20万交给李某,是委托他转交女方家庭,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李某私吞钱款,违反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构成违约。 案件中还涉及介绍费问题。农村习俗中确实存在“谢媒礼”,但李某收取5万元显然过高。不过小王父子自愿约定,且李某确实付出了跑腿辛苦,小王也愿意支付。在判决时,法院酌情认定,已付的3万元加上剩余2万元可在12万元中扣除,最终判决李某返还10万元。 这个案件,让人看到的不仅是钱,更是现实矛盾。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父母心急如焚,往往在巨额彩礼压力下病急乱投医。而婚姻介绍市场监管不足,部分媒人钻空子,收取高额费用,甚至截留彩礼,侵占利益。 类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河南某地,一名媒人虚构女方要价,多收10万元彩礼,法院同样认定属于不当得利,责令返还。江苏也有婚介公司无资质高额收费,被判退还。法律的态度很明确:婚姻介绍需合法合规,彩礼数额必须真实透明,不能成为谋取不义之财的手段。 这起案件也让人思考:为何彩礼总是矛盾的焦点?在一些地方,彩礼金额已经远远超出礼仪范畴,变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对农村家庭而言,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彩礼,往往掏空了全部积蓄。媒人看准这一点,以“女方要价”为由虚构金额,从中渔利。 法律上,彩礼不属于强制性规定,而是习俗。但《民法典》明确要求,民事行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彩礼数额过高,或以彩礼为幌子骗取财产,均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当得利。这也是司法判决的重要依据。 在小王的案子里,12万的损失最终靠法律追回。但背后的警示更值得注意:婚姻不是金钱的交易,媒人不能凌驾法律,财产往来必须有凭有据。否则,当亲情与信任被滥用,最终只会留下无休止的纠纷。 婚姻大事,本应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以彩礼金额论成败。彩礼可以有,但必须合理透明;媒人可以请,但必须依法合规。在这个故事里,小王赢得了官司,但更深的启示是,父母的婚姻焦虑不应成为别人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