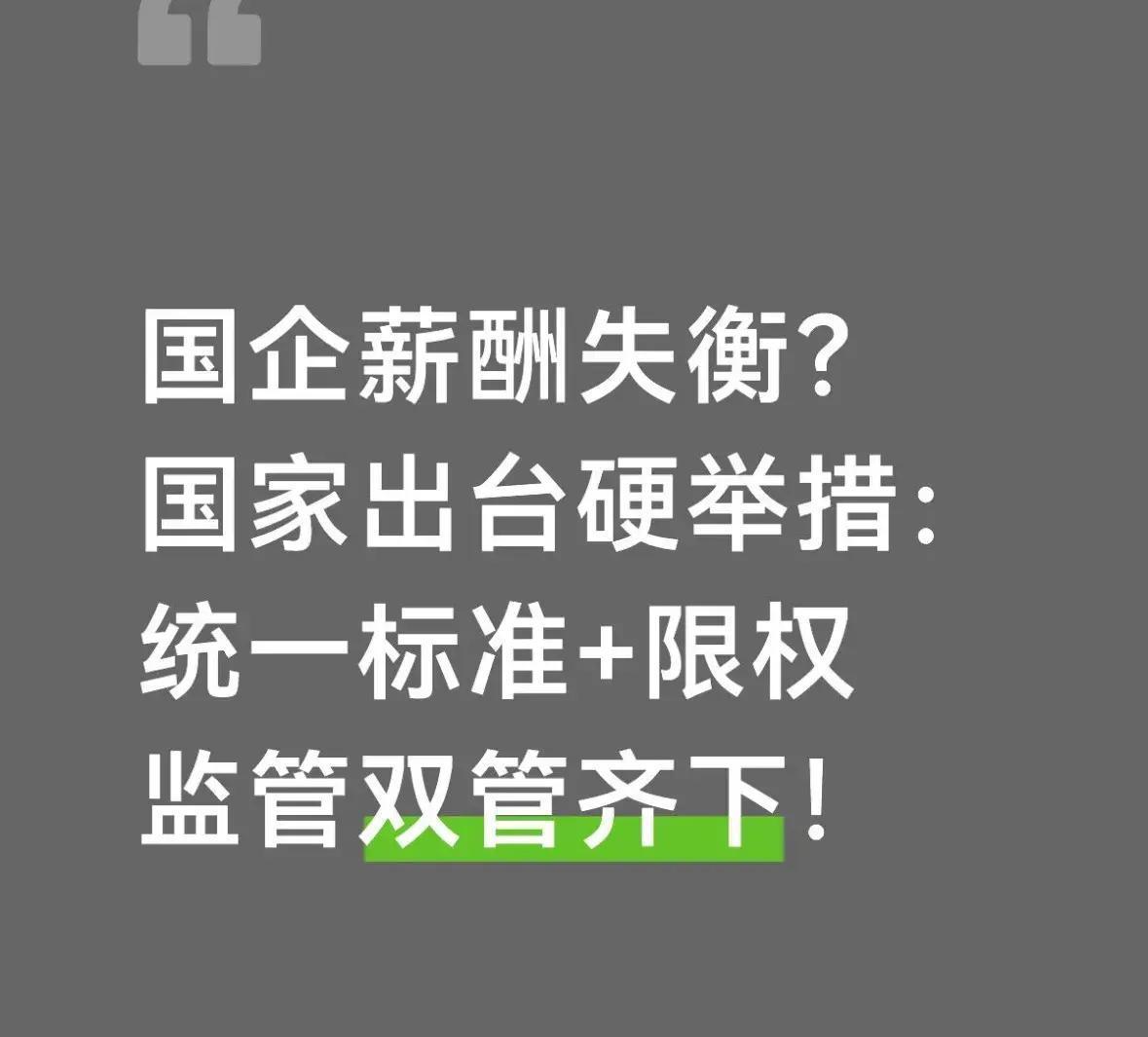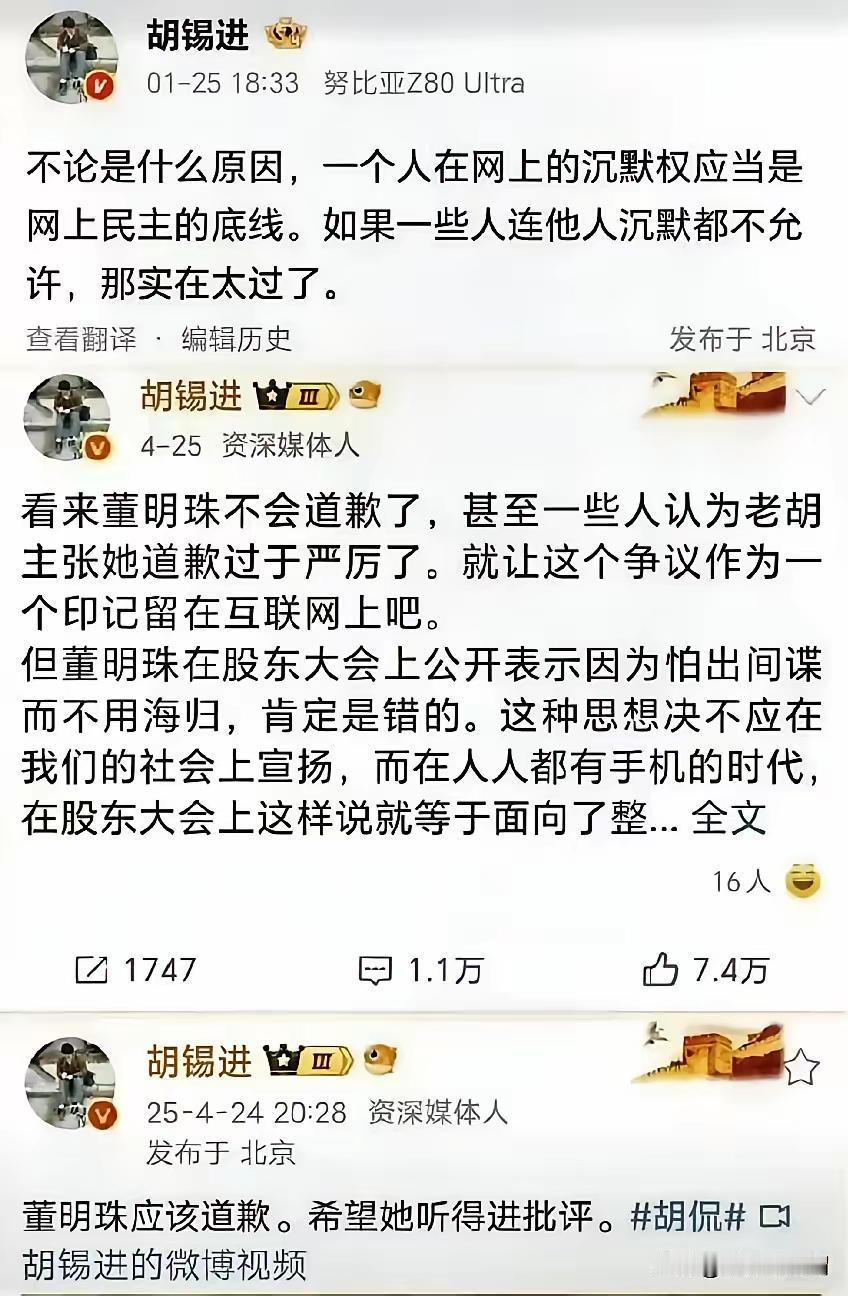董明珠说:“就得让有钱人多交点税。你看我年薪500万,扣掉45%的税,手里还能剩200多万呢,这钱够花了。可普通人一个月挣5000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根本不够用,个税起征点真该调到1万块。” 如果把讨论从网上的争吵里抽出来,放到一张最普通的办公桌上,其实更容易看明白:同样是“交个税”,不同收入人群的体感差得非常大。 一边是像董明珠这样的高收入管理者,她公开提到过自己的薪酬区间,大概在几百万元一年,按综合所得最高档税率计算,扣完税以后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对这类人来说,个税当然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占比很低,交完税仍然有足够的余量去安排储蓄、投资、改善型消费,所以更多是“比例高,但不至于影响生活运转”。 另一边是大量城市工薪人群,收入可能在每月五千到一万左右浮动,对他们来说,工资进账户后很快就会被固定支出切走:房租或房贷、通勤、吃饭、社保、公积金、孩子教育、家庭赡养,几乎每一项都很刚性。 个税占比也许不算特别高,但因为结余本来就薄,哪怕每月少几百元,到月底的压力差别,就会很明显。 也正因为结余有限,很多人对“起征点”这个数字会特别敏感——不是因为不愿意承担公共责任,而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他们每个月能留下多少缓冲。 董明珠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把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0000元,这个建议之所以每次都会引发讨论,核心就在于:起征点长期不动,而生活成本在变化。 2018年起征点调整到5000元后,后来确实增加了不少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 这些政策对一部分家庭有效,但并不能覆盖所有人,也不一定完全匹配每个人的真实支出结构。 更重要的是,很多开销在现实里是“刚涨不降”的:房租谈不上年年大幅上涨,但在不少城市想换到更通勤友好、居住条件更好的房子,成本很难变低。 养娃家庭的教育与托管支出弹性更小;日常消费即使单项涨幅不夸张,叠加起来也会让人明显感觉“同样的钱不经花”。 当起征点多年不变时,税负的体感,就可能变重——尤其对收入处在门槛附近的人来说,工资涨幅不大但开销持续上移,就会更容易出现“越忙越紧”的感觉。 从企业角度看,这个问题也会反映到用工上,企业给员工涨薪,真实目的往往是为了留人、让员工有获得感、有消费能力。 但当工资提高后,社保缴费基数、个税负担同步变化,再叠加物价和生活成本,员工到手增长不如预期,企业付出的成本却是实打实的。 管理者自然会觉得“不划算”:公司花了钱,但员工并没有因此更愿意留下。 反对提高起征点的人,常提一个点:如果大幅提高门槛,会不会让纳税人数量减少,从而影响财政收入。 这个担心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也容易把账算得过于“静态”,现实经济更像循环系统:居民手里多留下的钱,往往会以消费的方式回到市场,企业订单、服务业收入、增值税等也会随之变化。 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钱的用途通常更直接——不是拿去做复杂的资产配置,而是补在日常开销上:改善一顿饭、添置家电、给孩子报个课程、周末多一次出行,这类支出看似零碎,却最能带动需求。 另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争议点,是“谁在以什么方式交税”,董明珠这类以工资薪金为主的高收入者,税负相对透明,属于“发工资就扣税、很难绕开”的人群。 而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同收入来源,在税负结构上的差异:工薪所得适用超额累进,资本性所得、分红、某些经营性安排的实际税负和征管方式则更复杂。 普通工薪阶层最容易产生的不平衡感,往往不是“我交税你不交税”,而是“我的税扣得清清楚楚,你的收入形式更灵活、税负看起来更轻”,在这种背景下,单纯讨论起征点,会被放大成“公平问题”的讨论。 因此,把起征点提高到10000元的提议,表面上是一个数字调整,背后其实指向更现实的诉求:给处在中低收入区间、现金流紧张的人群留出更大余地,减少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脆弱感。 让税制在“主要盯劳动所得”之外,更多去回应公众对公平的感受——至少不要让“靠工资的人更痛、靠资本的人更轻”的印象持续固化。 税收当然需要稳定,也要支撑公共服务,但同样需要兼顾体感和公平,当一个制度让高收入者更多把它当作“正常义务”,却让不少普通上班族,把它当作“每月结余再被挤掉一块”,就说明政策讨论有必要继续往前走。 到底怎样调整更合理,起征点、扣除项目、税率结构、对不同收入来源的税负安排,哪些该一起改、怎么分步改,只有让多数人的现金流更有安全垫,消费才更敢发生。